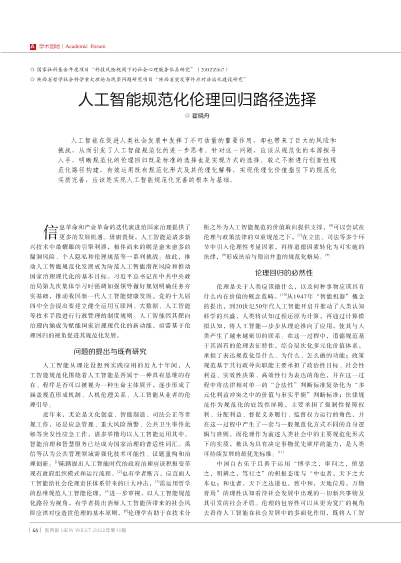人工智能规范化伦理回归路径选择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科技风险视阈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研究”(20BZZ067)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化建设研究”
人工智能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却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从而引发了人工智能规范化的进一步思考。针对这一问题,应该从规范化的本源探寻入手,明晰规范化的伦理回归既是标准的选择也是实现方式的选择。较之不断进行创新性规范化路径构建,有效运用既有规范化形式及其伦理化解释、实现伦理化价值指引下的规范化实质完善,应该是实现人工智能规范化完善的根本与基础。
信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演进给国家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是诸多新兴技术中最耀眼的引擎利器,相伴而来的则是愈来愈多的漏洞风险、个人隐私和伦理规范等一系列挑战。故此,推动人工智能规范化发展成为防范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人工智能因其靶向治理内涵成为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动能,亟需基于伦理回归的视角促进其规范化发展。
问题的提出与既有研究
人工智能从理论设想到实践应用的近九十年间,人工智能规范化围绕着人工智能是否属于一种具有思维的存在、程序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命主体展开,逐步形成了涵盖规范形成机制、人机伦理关系、人工智能从业者的伦理引导。
近年来,无论是文化创意、智能制造、司法公正等常规工作,还是应急管理、重大风险预警、公共卫生事件化解等突发性应急工作,诸多举措均以人工智能运用其中。智能治理和智慧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普适性词汇。禹信等认为公共管理领域需强化技术可能性、议题重构和治理创新。[1]陈鹏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应该积极变革现有政府组织模式和运行流程。[2]也有学者断言,应直面人工智能给社会伦理责任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3]需运用哲学的思维规范人工智能伦理。[4]进一步审视,以人工智能规范化路径为视角,有学者提出消解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应该对应造世伦理的基本原则,[5]伦理学有助于在技术分析之外为人工智能规范的价值取向提供支撑,[6]可以尝试在伦理与政策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7]在立法、司法等多个环节中引入伦理性考量因素,再将道德因素转化为可实施的法律,[8]形成法治与德治并重的规范化格局。[9]
伦理回归的必然性
伦理是关于人类应该做什么,以及何种事物应该具有什么内在价值的概念范畴。[10]从1947年“智能机器”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开启并推动了人类认知科学的兴盛,人类将认知过程还原为计算,再通过计算模拟认知,将人工智能一步步从理论推向了应用,使其与人类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道德规范基于其固有的伦理表征特性,综合层次化多元化价值体系,承担了表达规范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功能;政策规范基于其行政导向职能主要承担了政治性目标、社会性利益、实效性决策、高效性行为表达的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法律相对单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复杂化为“多元化利益冲突之中的价值与事实平衡”判断标准;法律规范作为规范化的底线性屏障,主要承担了强制性保障权利、分配利益、督促义务履行、监督权力运行的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套与一般规范化方式不同的自身逻辑与准则。而伦理作为前述人类社会中的主要规范化形式下的实质,被认为具有决定事物优先顺序的能力,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优先标准。[11]
中国自古乐于且善于运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积极态度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性认知看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切新兴事物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伦理的包容性可以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在社会发展中的多面化作用,既将人工智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化建设研究”
人工智能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却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从而引发了人工智能规范化的进一步思考。针对这一问题,应该从规范化的本源探寻入手,明晰规范化的伦理回归既是标准的选择也是实现方式的选择。较之不断进行创新性规范化路径构建,有效运用既有规范化形式及其伦理化解释、实现伦理化价值指引下的规范化实质完善,应该是实现人工智能规范化完善的根本与基础。
信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演进给国家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是诸多新兴技术中最耀眼的引擎利器,相伴而来的则是愈来愈多的漏洞风险、个人隐私和伦理规范等一系列挑战。故此,推动人工智能规范化发展成为防范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人工智能因其靶向治理内涵成为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动能,亟需基于伦理回归的视角促进其规范化发展。
问题的提出与既有研究
人工智能从理论设想到实践应用的近九十年间,人工智能规范化围绕着人工智能是否属于一种具有思维的存在、程序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命主体展开,逐步形成了涵盖规范形成机制、人机伦理关系、人工智能从业者的伦理引导。
近年来,无论是文化创意、智能制造、司法公正等常规工作,还是应急管理、重大风险预警、公共卫生事件化解等突发性应急工作,诸多举措均以人工智能运用其中。智能治理和智慧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普适性词汇。禹信等认为公共管理领域需强化技术可能性、议题重构和治理创新。[1]陈鹏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应该积极变革现有政府组织模式和运行流程。[2]也有学者断言,应直面人工智能给社会伦理责任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3]需运用哲学的思维规范人工智能伦理。[4]进一步审视,以人工智能规范化路径为视角,有学者提出消解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应该对应造世伦理的基本原则,[5]伦理学有助于在技术分析之外为人工智能规范的价值取向提供支撑,[6]可以尝试在伦理与政策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7]在立法、司法等多个环节中引入伦理性考量因素,再将道德因素转化为可实施的法律,[8]形成法治与德治并重的规范化格局。[9]
伦理回归的必然性
伦理是关于人类应该做什么,以及何种事物应该具有什么内在价值的概念范畴。[10]从1947年“智能机器”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开启并推动了人类认知科学的兴盛,人类将认知过程还原为计算,再通过计算模拟认知,将人工智能一步步从理论推向了应用,使其与人类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道德规范基于其固有的伦理表征特性,综合层次化多元化价值体系,承担了表达规范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功能;政策规范基于其行政导向职能主要承担了政治性目标、社会性利益、实效性决策、高效性行为表达的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法律相对单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复杂化为“多元化利益冲突之中的价值与事实平衡”判断标准;法律规范作为规范化的底线性屏障,主要承担了强制性保障权利、分配利益、督促义务履行、监督权力运行的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套与一般规范化方式不同的自身逻辑与准则。而伦理作为前述人类社会中的主要规范化形式下的实质,被认为具有决定事物优先顺序的能力,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优先标准。[11]
中国自古乐于且善于运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积极态度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性认知看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切新兴事物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伦理的包容性可以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在社会发展中的多面化作用,既将人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