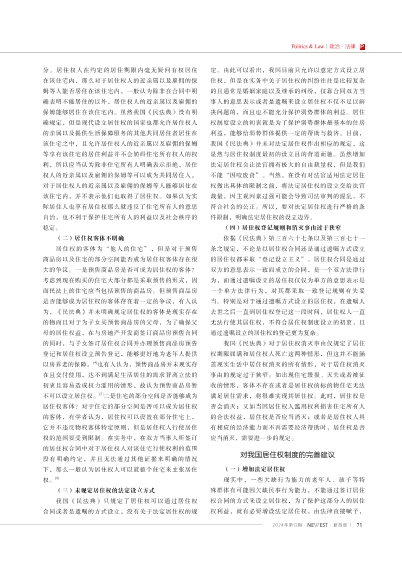我国居住权制度探析
分。居住权人在约定的居住期限内毫无疑问有权居住在该住宅内,那么对于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等人能否居住在该住宅内,一般认为除非在合同中明确表明不能居住的以外,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能够居住在该住宅内。虽然我国《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但是现代设立居住权的国家也都允许居住权人的亲属以及提供生活保障服务的其他共同居住者居住在该住宅之中,且允许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等享有该住宅的居住利益并不会妨碍住宅所有权人的权利,所以应当认为除非住宅所有人明确表示拒绝,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等可以成为共同居住人。对于居住权人的近亲属以及雇佣的保姆等人能够居住在该住宅内,并不表示他们也取得了居住权。如果认为实际居住人也享有居住权那么就违反了住宅所有人的意思自治,也不利于保护住宅所有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居住权客体不明确
居住权的客体为“他人的住宅”,但是对于预售商品房以及住宅的部分空间能否成为居住权客体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是预售商品房是否可成为居住权的客体?考虑到现在购买的住宅大部分都是采取预售的形式,因而民法上的住宅应当包括预售的商品房。但预售商品房是否能够成为居住权的客体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居住权的客体是现实存在的物而且对于为子女买预售商品房的父母,为了确保父母的居住权益,在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同时,与子女签订居住权合同并办理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和居住权设立预告登记,能够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以房养老的保障。[4]也有人认为,预售商品房并未现实存在且交付使用,达不到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背离立法的初衷且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的情形,故认为预售商品房暂不可以设立居住权。[5]二是住宅的部分空间是否能够成为居住权客体?对于住宅的部分空间是否可以成为居住权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居住权可以设置在部分住宅上,它并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但是居住权人行使居住权的范围要受到限制。在实务中,在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居住权合同中对于居住权人对该住宅行使权利的范围没有明确约定,并且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来明确的情况下,那么一般认为居住权人可以就整个住宅来主张居住权。[6]
(三)未规定居住权的法定设立方式
我国《民法典》只规定了居住权可以通过居住权合同或者是遗嘱的方式设立,没有关于法定居住权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只允许以意定方式设立居住权,但是在实务中关于居住权的纠纷往往是比较复杂的且通常是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的纠纷,仅靠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者是遗嘱来设立居住权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而且也不能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最基本的住房利益,能够给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救济。目前,我国《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居住权作出相应的规定,这显然与居住权制度最初的设立目的背道而驰。虽然增加法定居住权会让法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当然,在没有对法官适用法定居住权做出具体的限制之前,将法定居住权的设立交给法官裁量,因主观因素过强可能会导致司法审判的混乱,不符合社会的公正。所以,要对法定居住权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制,明确法定居住权的设立边界。
(四)居住权登记规则和消灭事由过于狭窄
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以及第三百七十一条之规定,不论是以居住权合同还是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都采取“登记设立主义”。居住权合同是通过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合同,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而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仅仅为单方的意思表示是一个单方法律行为,对其都采取一致登记规则有失妥当。特别是对于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在遗嘱人去世之后一直到居住权登记这一段时间,居住权人一直无法行使其居住权,不符合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初衷,且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的登记更为复杂。
我国《民法典》对于居住权消灭事由仅规定了居住权期限届满和居住权人死亡这两种情形,但这并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居住权消灭的所有情形,对于居住权消灭事由的规定过于狭窄。如出现住宅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的情形,客体不存在或者是居住权的标的物住宅无法满足居住需求,将很难实现其居住权。此时,居住权是否会消灭;又如当因居住权人滥用权利损害住宅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居住权是否应当消灭;或者是居住权人具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而不再需要经济帮助时,居住权是否应当消灭,需要进一步的规定。
对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增加法定居住权
现实中,一些欠缺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孩子等特殊群体有可能因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不能通过签订居住权合同的方式来设立居住权,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居住权利益,就有必要增设法定居住权,由法律直接赋予,
(二)居住权客体不明确
居住权的客体为“他人的住宅”,但是对于预售商品房以及住宅的部分空间能否成为居住权客体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是预售商品房是否可成为居住权的客体?考虑到现在购买的住宅大部分都是采取预售的形式,因而民法上的住宅应当包括预售的商品房。但预售商品房是否能够成为居住权的客体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居住权的客体是现实存在的物而且对于为子女买预售商品房的父母,为了确保父母的居住权益,在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同时,与子女签订居住权合同并办理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和居住权设立预告登记,能够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以房养老的保障。[4]也有人认为,预售商品房并未现实存在且交付使用,达不到满足生活居住的需求背离立法的初衷且容易造成权力滥用的情形,故认为预售商品房暂不可以设立居住权。[5]二是住宅的部分空间是否能够成为居住权客体?对于住宅的部分空间是否可以成为居住权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居住权可以设置在部分住宅上,它并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但是居住权人行使居住权的范围要受到限制。在实务中,在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居住权合同中对于居住权人对该住宅行使权利的范围没有明确约定,并且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来明确的情况下,那么一般认为居住权人可以就整个住宅来主张居住权。[6]
(三)未规定居住权的法定设立方式
我国《民法典》只规定了居住权可以通过居住权合同或者是遗嘱的方式设立,没有关于法定居住权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只允许以意定方式设立居住权,但是在实务中关于居住权的纠纷往往是比较复杂的且通常是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的纠纷,仅靠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者是遗嘱来设立居住权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而且也不能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最基本的住房利益,能够给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救济。目前,我国《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居住权作出相应的规定,这显然与居住权制度最初的设立目的背道而驰。虽然增加法定居住权会让法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当然,在没有对法官适用法定居住权做出具体的限制之前,将法定居住权的设立交给法官裁量,因主观因素过强可能会导致司法审判的混乱,不符合社会的公正。所以,要对法定居住权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制,明确法定居住权的设立边界。
(四)居住权登记规则和消灭事由过于狭窄
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以及第三百七十一条之规定,不论是以居住权合同还是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都采取“登记设立主义”。居住权合同是通过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合同,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而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仅仅为单方的意思表示是一个单方法律行为,对其都采取一致登记规则有失妥当。特别是对于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在遗嘱人去世之后一直到居住权登记这一段时间,居住权人一直无法行使其居住权,不符合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初衷,且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的登记更为复杂。
我国《民法典》对于居住权消灭事由仅规定了居住权期限届满和居住权人死亡这两种情形,但这并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居住权消灭的所有情形,对于居住权消灭事由的规定过于狭窄。如出现住宅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的情形,客体不存在或者是居住权的标的物住宅无法满足居住需求,将很难实现其居住权。此时,居住权是否会消灭;又如当因居住权人滥用权利损害住宅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居住权是否应当消灭;或者是居住权人具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而不再需要经济帮助时,居住权是否应当消灭,需要进一步的规定。
对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增加法定居住权
现实中,一些欠缺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孩子等特殊群体有可能因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不能通过签订居住权合同的方式来设立居住权,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居住权利益,就有必要增设法定居住权,由法律直接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