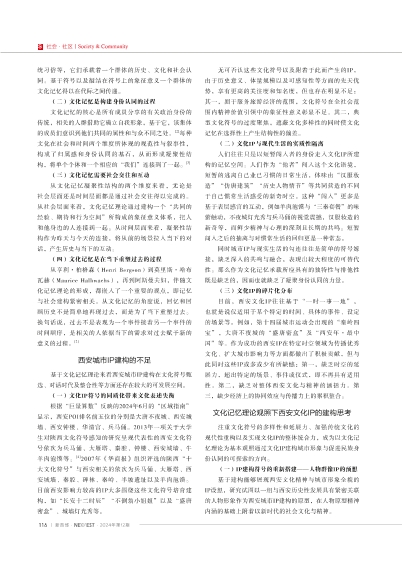文化记忆理论观照下西安城市IP建构的不足及应对策略
统习俗等,它们承载着一个群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认同。基于符号以及凝结在符号上的象征意义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得以在代际之间传递。
(二)文化记忆是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
文化记忆的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2]每种文化在社会和时间两个维度所体现的规范性与叙事性,构成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石,从而形成凝聚性结构,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了一起。[3]
(三)文化记忆需要社会交往和互动
从文化记忆凝聚性结构的两个维度来看,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时间层面都是通过社会交往得以完成的。从社会层面来看,文化记忆理论通过建构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所构成的象征意义体系,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从时间层面来看,凝聚性结构作为昨天与今天的连接,将从前的场景拉入当下的对话,产生历史与当下的互动。
(四)文化记忆是在当下重塑过去的过程
从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到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再到阿斯曼夫妇,伴随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都嵌入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记忆与社会建构紧密相关。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说,回忆和回顾历史不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为了当下重塑过去。换句话说,过去不是表现为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事件的时间顺序,是相关的人依据当下的需求对过去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2]
西安城市IP建构的不足
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来看西安城市IP建构在文化符号甄选、对话时代及整合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可发展空间。
(一)文化IP符号的同质化带来文化表述失衡
根据“巨量算数”反映的2024年6月的“区域指南”显示,西安POI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大唐不夜城、西安城墙、西安钟楼、华清宫、兵马俑。2013年一项关于大学生对陕西文化符号感知的研究呈现代表性的西安文化符号依次为兵马俑、大雁塔、秦腔、钟楼、西安城墙、牛羊肉泡馍等。[4]2007年《华商报》组织评选的陕西“十大文化符号”与西安相关的依次为兵马俑、大雁塔、西安城墙、秦腔、碑林、秦岭、半坡遗址以及羊肉泡馍。目前西安影响力较高的IP大多围绕这些文化符号培育建构,如“长安十二时辰”“不倒翁小姐姐”以及“盛唐密盒”、城墙灯光秀等。
无可否认这些文化符号以及附着于此而产生的IP,由于历史意义、体量规模以及可感知性等方面的先天优势,享有更高的关注度和知名度,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其一,囿于服务旅游经济的范围,文化符号在全社会范围内精神价值引领中的象征性意义彰显不足。其二,典型文化符号的过度聚焦,遮蔽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使文化记忆在选择性上产生结构性的偏差。
(二)文化IP与现代生活的实质性隔离
人们往往只是以短暂闯入者的身份走入文化IP所建构的记忆空间。人们作为“他者”闯入这个文化语境,短暂的逃离自己业已习惯的日常生活,体味由“汉服妆造”“仿唐建筑”“历史人物情节”等共同营造的不同于自己惯常生活感受的新奇时空。这种“闯入”更多是基于表层感官的互动,例如羊肉泡馍与“三秦套餐”的味蕾触动,不夜城灯光秀与兵马俑的视觉震撼,汉服妆造的新奇等,而鲜少精神与心理的深刻且长期的共鸣。短暂闯入之后的抽离与对惯常生活的回归更是一种常态。
同时城市IP与现实生活的勾连往往是简单的符号嫁接,缺乏深入的共鸣与融合,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可替代性。那么作为文化记忆承载所应具有的独特性与排他性既是缺乏的,因而也就缺乏了凝聚身份认同的力量。
(三)文化IP的碎片化分布
目前,西安文化IP往往基于“一时一事一地”,也就是说仅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具体的事件、设定的场景等。例如,第十四届城市运动会出现的“秦岭四宝”,大唐不夜城的“盛唐密盒”及“西安年·最中国”等。作为成功的西安IP在特定时空领域为传播优秀文化、扩大城市影响力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这些IP或多或少有所缺憾:第一,缺乏时空的延展力,超出特定的场景、事件或仪式,即不再具有适用性。第二,缺乏对整体西安文化与精神的涵括力。第三,缺少经济上的协同效应与传播力上的累积整合。
文化记忆理论观照下西安文化IP的建构思考
注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和延展力、加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构以及实现文化IP的整体统合力,成为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本观照通过文化IP建构城市形象与促进民族身份认同的可探索的方向。
(一)IP建构符号的重新搭建——人物群像IP的预想
基于建构能够展现西安文化精神与城市形象全貌的IP设想,研究试图以一组与西安历史性发展具有紧密关联的人物形象作为西安城市IP建构的原型,在人物原型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附着以新时代的社会文化与精神。
(二)文化记忆是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
文化记忆的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2]每种文化在社会和时间两个维度所体现的规范性与叙事性,构成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石,从而形成凝聚性结构,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了一起。[3]
(三)文化记忆需要社会交往和互动
从文化记忆凝聚性结构的两个维度来看,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时间层面都是通过社会交往得以完成的。从社会层面来看,文化记忆理论通过建构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所构成的象征意义体系,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从时间层面来看,凝聚性结构作为昨天与今天的连接,将从前的场景拉入当下的对话,产生历史与当下的互动。
(四)文化记忆是在当下重塑过去的过程
从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到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再到阿斯曼夫妇,伴随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都嵌入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记忆与社会建构紧密相关。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说,回忆和回顾历史不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为了当下重塑过去。换句话说,过去不是表现为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事件的时间顺序,是相关的人依据当下的需求对过去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2]
西安城市IP建构的不足
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来看西安城市IP建构在文化符号甄选、对话时代及整合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可发展空间。
(一)文化IP符号的同质化带来文化表述失衡
根据“巨量算数”反映的2024年6月的“区域指南”显示,西安POI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大唐不夜城、西安城墙、西安钟楼、华清宫、兵马俑。2013年一项关于大学生对陕西文化符号感知的研究呈现代表性的西安文化符号依次为兵马俑、大雁塔、秦腔、钟楼、西安城墙、牛羊肉泡馍等。[4]2007年《华商报》组织评选的陕西“十大文化符号”与西安相关的依次为兵马俑、大雁塔、西安城墙、秦腔、碑林、秦岭、半坡遗址以及羊肉泡馍。目前西安影响力较高的IP大多围绕这些文化符号培育建构,如“长安十二时辰”“不倒翁小姐姐”以及“盛唐密盒”、城墙灯光秀等。
无可否认这些文化符号以及附着于此而产生的IP,由于历史意义、体量规模以及可感知性等方面的先天优势,享有更高的关注度和知名度,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其一,囿于服务旅游经济的范围,文化符号在全社会范围内精神价值引领中的象征性意义彰显不足。其二,典型文化符号的过度聚焦,遮蔽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使文化记忆在选择性上产生结构性的偏差。
(二)文化IP与现代生活的实质性隔离
人们往往只是以短暂闯入者的身份走入文化IP所建构的记忆空间。人们作为“他者”闯入这个文化语境,短暂的逃离自己业已习惯的日常生活,体味由“汉服妆造”“仿唐建筑”“历史人物情节”等共同营造的不同于自己惯常生活感受的新奇时空。这种“闯入”更多是基于表层感官的互动,例如羊肉泡馍与“三秦套餐”的味蕾触动,不夜城灯光秀与兵马俑的视觉震撼,汉服妆造的新奇等,而鲜少精神与心理的深刻且长期的共鸣。短暂闯入之后的抽离与对惯常生活的回归更是一种常态。
同时城市IP与现实生活的勾连往往是简单的符号嫁接,缺乏深入的共鸣与融合,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可替代性。那么作为文化记忆承载所应具有的独特性与排他性既是缺乏的,因而也就缺乏了凝聚身份认同的力量。
(三)文化IP的碎片化分布
目前,西安文化IP往往基于“一时一事一地”,也就是说仅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具体的事件、设定的场景等。例如,第十四届城市运动会出现的“秦岭四宝”,大唐不夜城的“盛唐密盒”及“西安年·最中国”等。作为成功的西安IP在特定时空领域为传播优秀文化、扩大城市影响力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这些IP或多或少有所缺憾:第一,缺乏时空的延展力,超出特定的场景、事件或仪式,即不再具有适用性。第二,缺乏对整体西安文化与精神的涵括力。第三,缺少经济上的协同效应与传播力上的累积整合。
文化记忆理论观照下西安文化IP的建构思考
注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和延展力、加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构以及实现文化IP的整体统合力,成为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本观照通过文化IP建构城市形象与促进民族身份认同的可探索的方向。
(一)IP建构符号的重新搭建——人物群像IP的预想
基于建构能够展现西安文化精神与城市形象全貌的IP设想,研究试图以一组与西安历史性发展具有紧密关联的人物形象作为西安城市IP建构的原型,在人物原型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附着以新时代的社会文化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