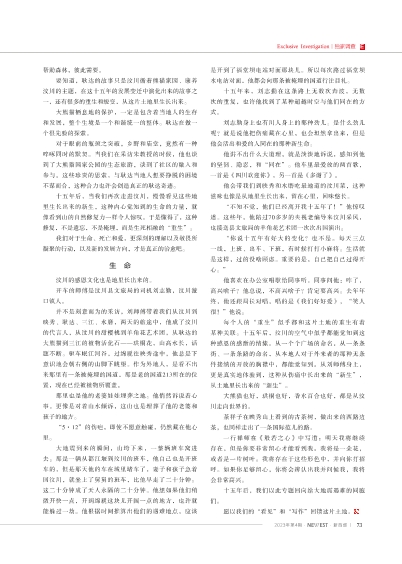土地里长出来的“新生”
帮助森林,彼此需要。
要知道,耿达的故事只是汶川循着熊猫家园、康养汶川的主题,在这十五年的发展变迁中演化出来的故事之一,还有很多的重生和蜕变,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
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一定是包含着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整个生境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耿达在做一个很先验的探索。
对于眼前的瓶颈之突破,乡野和庙堂,竟然有一种啐啄同时的默契。当我们在采访朱教授的时候,他也谈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谈到了社区的融入和参与。这些珍贵的思索,与耿达当地人想要挣脱的困境不谋而合,这种合力也许会创造真正的耿达奇迹。
十五年后,当我们再次走进汶川,慢慢看见这些地里生长出来的新生,这种内心觉知到的生命的力量,就像看到山的自然修复力一样令人惊叹。于是懂得了,这种修复,不是遗忘,不是掩埋,而是生死相融的“重生”。
我们对于生命、死亡和爱,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敬畏所凝聚的行动,以及新的发展方向,才是真正的治愈吧。
生 命
汶川的感恩文化也是地里长出来的。
开车的师傅是汶川县文旅局的司机刘志勤,汶川漩口镇人。
并不是刻意而为的采访,刘师傅带着我们从汶川到映秀、耿达、三江、水磨,两天的旅途中,他成了汶川的代言人,从汶川的甜樱桃到羊角花艺术团,从耿达的大熊猫到三江的植物活化石——珙桐花,山高水长,话题不断。驱车岷江河谷,过绵虒往映秀途中,他总是下意识地会朝右侧的山脚下眺望。作为外地人,是看不出来那里有一条被掩埋的国道,那是老的国道213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被植物所覆盖。
那里也是他的老婆娃娃埋葬之地。他悄然诉说着心事。更像是对着山水倾诉,这山也是埋葬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的地方。
“5·12”的伤疤,即使不愿意触碰,仍然藏在他心里。
大地震到来的瞬间,山垮下来,一整辆班车窝进去。那是一辆从都江堰到汶川的班车,他自己也是开班车的,但是那天他的车在城里堵车了,妻子和孩子急着回汶川,就坐上了舅舅的班车,比他早走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成了天人永隔的二十分钟。他想如果他们稍微开快一点,开到绵虒这块儿开阔一点的地方,也许就能躲过一劫。他根据时间推算出他们的遇难地点,应该是开到了福堂坝电站对面那块儿。所以每次路过福堂坝水电站对面,他都会向那条被掩埋的国道行注目礼。
十五年来,刘志勤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奔波,无数次的重复,也许他找到了某种超越时空与他们同在的方式。
刘志勤身上也有川人身上的那种劲儿。是什么劲儿呢?就是说他把伤痛藏在心里,也会坦然拿出来,但是他会活出和爱的人同在的那种新生命。
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淡淡地诉说,感知到他的坚韧、隐忍,和“同在”。他车里最爱放的两首歌,一首是《四川欢迎你》,另一首是《多谢了》。
他会带我们到映秀和水磨吃最地道的汶川菜,这种滋味也像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留在心里,回味悠长。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他惊叹道。这些年,他陪过70多岁的央视老编导来汶川采风,也接送县文旅局的羊角花艺术团一次次出国演出。
“你说十五年有好大的变化?也不是。每天三点一线,上班、出车、下班,有时候打打小麻将。生活就是这样,过的没啥顾虑。重要的是,自己把自己过得开心。”
他喜欢在办公室唱歌给同事听。同事问他:咋了,高兴啥子?他总说,不高兴啥子?肯定要高兴。去年年终,他还跟局长对唱,唱的是《我们好好爱》,“笑人很!”他说。
每个人的“重生”似乎都和这片土地的重生有着某种关联。十五年后,汶川的空气中似乎都能觉知到这种感恩的感激的情愫。从一个个广场的命名,从一条条街、一条条路的命名,从本地人对于外来者的那种无条件接纳的开放的胸襟中,都能觉知到。从刘师傅身上,更是真实地体验到,这种从伤痛中长出来的“新生”,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新生”。
大熊猫也好,珙桐也好,香水百合也好,都是从汶川走向世界的。
茶祥子在映秀山上看到的古茶树,做出来的西路边茶,也同样走出了一条国际范儿的路。
一行禅师在《般若之心》中写道:明天我将继续存在,但是你要非常留心才能看到我。我将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片树叶。我将存在于这些形色中,并向你打招呼。如果你足够留心,你将会辨认出我并问候我,我将会非常高兴。
十五年后,我们以此专题回向给大地震遇难的同胞们。
愿以我们的“看见”和“写作”回馈这片土地。
要知道,耿达的故事只是汶川循着熊猫家园、康养汶川的主题,在这十五年的发展变迁中演化出来的故事之一,还有很多的重生和蜕变,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
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一定是包含着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整个生境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耿达在做一个很先验的探索。
对于眼前的瓶颈之突破,乡野和庙堂,竟然有一种啐啄同时的默契。当我们在采访朱教授的时候,他也谈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谈到了社区的融入和参与。这些珍贵的思索,与耿达当地人想要挣脱的困境不谋而合,这种合力也许会创造真正的耿达奇迹。
十五年后,当我们再次走进汶川,慢慢看见这些地里生长出来的新生,这种内心觉知到的生命的力量,就像看到山的自然修复力一样令人惊叹。于是懂得了,这种修复,不是遗忘,不是掩埋,而是生死相融的“重生”。
我们对于生命、死亡和爱,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敬畏所凝聚的行动,以及新的发展方向,才是真正的治愈吧。
生 命
汶川的感恩文化也是地里长出来的。
开车的师傅是汶川县文旅局的司机刘志勤,汶川漩口镇人。
并不是刻意而为的采访,刘师傅带着我们从汶川到映秀、耿达、三江、水磨,两天的旅途中,他成了汶川的代言人,从汶川的甜樱桃到羊角花艺术团,从耿达的大熊猫到三江的植物活化石——珙桐花,山高水长,话题不断。驱车岷江河谷,过绵虒往映秀途中,他总是下意识地会朝右侧的山脚下眺望。作为外地人,是看不出来那里有一条被掩埋的国道,那是老的国道213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被植物所覆盖。
那里也是他的老婆娃娃埋葬之地。他悄然诉说着心事。更像是对着山水倾诉,这山也是埋葬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的地方。
“5·12”的伤疤,即使不愿意触碰,仍然藏在他心里。
大地震到来的瞬间,山垮下来,一整辆班车窝进去。那是一辆从都江堰到汶川的班车,他自己也是开班车的,但是那天他的车在城里堵车了,妻子和孩子急着回汶川,就坐上了舅舅的班车,比他早走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成了天人永隔的二十分钟。他想如果他们稍微开快一点,开到绵虒这块儿开阔一点的地方,也许就能躲过一劫。他根据时间推算出他们的遇难地点,应该是开到了福堂坝电站对面那块儿。所以每次路过福堂坝水电站对面,他都会向那条被掩埋的国道行注目礼。
十五年来,刘志勤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奔波,无数次的重复,也许他找到了某种超越时空与他们同在的方式。
刘志勤身上也有川人身上的那种劲儿。是什么劲儿呢?就是说他把伤痛藏在心里,也会坦然拿出来,但是他会活出和爱的人同在的那种新生命。
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淡淡地诉说,感知到他的坚韧、隐忍,和“同在”。他车里最爱放的两首歌,一首是《四川欢迎你》,另一首是《多谢了》。
他会带我们到映秀和水磨吃最地道的汶川菜,这种滋味也像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留在心里,回味悠长。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他惊叹道。这些年,他陪过70多岁的央视老编导来汶川采风,也接送县文旅局的羊角花艺术团一次次出国演出。
“你说十五年有好大的变化?也不是。每天三点一线,上班、出车、下班,有时候打打小麻将。生活就是这样,过的没啥顾虑。重要的是,自己把自己过得开心。”
他喜欢在办公室唱歌给同事听。同事问他:咋了,高兴啥子?他总说,不高兴啥子?肯定要高兴。去年年终,他还跟局长对唱,唱的是《我们好好爱》,“笑人很!”他说。
每个人的“重生”似乎都和这片土地的重生有着某种关联。十五年后,汶川的空气中似乎都能觉知到这种感恩的感激的情愫。从一个个广场的命名,从一条条街、一条条路的命名,从本地人对于外来者的那种无条件接纳的开放的胸襟中,都能觉知到。从刘师傅身上,更是真实地体验到,这种从伤痛中长出来的“新生”,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新生”。
大熊猫也好,珙桐也好,香水百合也好,都是从汶川走向世界的。
茶祥子在映秀山上看到的古茶树,做出来的西路边茶,也同样走出了一条国际范儿的路。
一行禅师在《般若之心》中写道:明天我将继续存在,但是你要非常留心才能看到我。我将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片树叶。我将存在于这些形色中,并向你打招呼。如果你足够留心,你将会辨认出我并问候我,我将会非常高兴。
十五年后,我们以此专题回向给大地震遇难的同胞们。
愿以我们的“看见”和“写作”回馈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