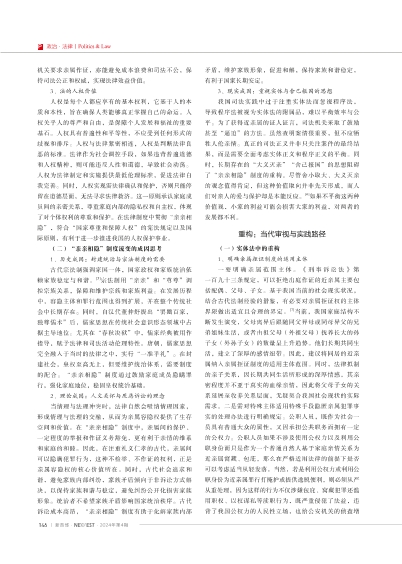“亲亲相隐”制度的结构、解构与重构
机关要求亲属作证,亦能避免成本浪费和司法不公,保持司法公正和权威,实现法律效益价值。
3、法的人权价值
人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基于人的本质和本性,旨在确保人类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人权关乎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保障个人发展和福祉的重要基石。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排斥。人权与法律紧密相连,人权是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法律作为社会调控手段,如果违背普遍道德和人权精神,则可能违反人性和道德,导致社会动荡。人权为法律制定和实施提供最低伦理标准,促进法律自我完善。同时,人权实现需法律确认和保护,否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无法寻求法律救济。这一原则承认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尊重家庭内部的隐私权和自主权,体现了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法律制度中贯彻“亲亲相隐”,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以及国际原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人权保护事业。
(二)“亲亲相隐”制度流变的成因思考
1、历史成因:封建统治与宗法制度的需要
古代宗法制强调家国一体,国家政权和家族统治依赖家族稳定与和谐。[5]宗法制用“亲亲”和“尊尊”调控宗族关系,保障和维护宗族和家族利益。在发展历程中,容隐主体和罪行范围也得到扩展,并在整个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同时,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春秋决狱”中,儒家经典被用作指导,赋予法律和司法活动伦理特性。唐朝,儒家思想完全融入于当时的法律之中,实行“一准乎礼”。在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但要维护统治体系,需要制度的配合。“亲亲相隐”制度通过鼓励家庭成员隐瞒罪行,强化家庭地位,稳固皇权统治基础。
2、理论成因:人文关怀与厌恶诉讼的理念
当情理与法理冲突时,法律自然会吸纳情理因素,形成情理与法理的交融,从而为亲属容隐权提供了生存空间和价值。在“亲亲相隐”制度中,亲属间的保护、一定程度的举报和作证义务豁免,更有利于亲情的维系和家庭的和睦。因此,在注重礼义仁孝的古代,亲属间可以隐瞒犯罪行为,这种不检举、不作证的权利,正是亲属容隐权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古代社会追求和谐,避免家族内部纠纷,家族矛盾倾向于非诉讼方式解决,以保持家族和谐与稳定,避免纠纷公开化损害家族形象。统治者不希望家族矛盾影响国家统治秩序。古代诉讼成本高昂,“亲亲相隐”制度有助于化解家族内部矛盾,维护家族形象,促进和解,保持家族和谐稳定,有利于国家长期安定。
3、现实成因:重视实体与舍己报国的思想
我国司法实践中过于注重实体法而忽视程序法,导致程序法被视为实体法的附属品,难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了获得近亲属的证人证言,司法机关采取了鼓励甚至“逼迫”的方法。虽然查明案情很重要,但不应牺牲人伦亲情。真正的司法正义并非只关注案件的最终结果,而是需要全面考虑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同时,长期存在的“大义灭亲”“舍己报国”的思想阻碍了“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尽管舍小取大、大义灭亲的观念值得肯定,但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先天形成,而人们对亲人的爱与保护却是本能反应。[6]如果不平衡这两种价值观,小家的利益可能会损害大家的利益,对两者的发展都不利。
重构:当代审视与实践路径
(一)实体法中的重构
1、明确亲属拒证制度的适用主体
一要明确亲属范围主体。《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可以拒绝出庭作证的近亲属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结合古代法制经验的借鉴,有必要对亲属拒证权的主体界限做出适宜且合理的界定。[7]当前,我国家庭结构不断发生演变,父母离异后跟随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生活,或者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长大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纽带。因此,建议将同居的近亲属纳入亲属拒证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同时,法律拟制的亲子关系,因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深厚情感,其亲密程度并不亚于真实的血缘亲情,因此将父母子女的关系延展至收养关系层面,无疑契合我国社会现状的实际需求。二是需对特殊主体适用特殊手段隐匿亲属犯罪事实的处理办法进行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既作为社会一员具有普通大众的属性,又因承担公共职务而拥有一定的公权力。公职人员如果不涉及使用公权力以及利用公职身份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自然人基于家庭亲情关系为近亲属窝藏、包庇,那么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发落。当然,若是利用公权力或利用公职身份为近亲属罪行打掩护或提供逃脱便利,则必须从严从重处理,因为这样的行为不仅涉嫌包庇、窝藏犯罪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渎职行为,既严重侵犯了法益,违背了我国公权力的人民性立场,也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增
3、法的人权价值
人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基于人的本质和本性,旨在确保人类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人权关乎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保障个人发展和福祉的重要基石。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排斥。人权与法律紧密相连,人权是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法律作为社会调控手段,如果违背普遍道德和人权精神,则可能违反人性和道德,导致社会动荡。人权为法律制定和实施提供最低伦理标准,促进法律自我完善。同时,人权实现需法律确认和保护,否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无法寻求法律救济。这一原则承认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尊重家庭内部的隐私权和自主权,体现了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法律制度中贯彻“亲亲相隐”,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以及国际原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人权保护事业。
(二)“亲亲相隐”制度流变的成因思考
1、历史成因:封建统治与宗法制度的需要
古代宗法制强调家国一体,国家政权和家族统治依赖家族稳定与和谐。[5]宗法制用“亲亲”和“尊尊”调控宗族关系,保障和维护宗族和家族利益。在发展历程中,容隐主体和罪行范围也得到扩展,并在整个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同时,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春秋决狱”中,儒家经典被用作指导,赋予法律和司法活动伦理特性。唐朝,儒家思想完全融入于当时的法律之中,实行“一准乎礼”。在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但要维护统治体系,需要制度的配合。“亲亲相隐”制度通过鼓励家庭成员隐瞒罪行,强化家庭地位,稳固皇权统治基础。
2、理论成因:人文关怀与厌恶诉讼的理念
当情理与法理冲突时,法律自然会吸纳情理因素,形成情理与法理的交融,从而为亲属容隐权提供了生存空间和价值。在“亲亲相隐”制度中,亲属间的保护、一定程度的举报和作证义务豁免,更有利于亲情的维系和家庭的和睦。因此,在注重礼义仁孝的古代,亲属间可以隐瞒犯罪行为,这种不检举、不作证的权利,正是亲属容隐权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古代社会追求和谐,避免家族内部纠纷,家族矛盾倾向于非诉讼方式解决,以保持家族和谐与稳定,避免纠纷公开化损害家族形象。统治者不希望家族矛盾影响国家统治秩序。古代诉讼成本高昂,“亲亲相隐”制度有助于化解家族内部矛盾,维护家族形象,促进和解,保持家族和谐稳定,有利于国家长期安定。
3、现实成因:重视实体与舍己报国的思想
我国司法实践中过于注重实体法而忽视程序法,导致程序法被视为实体法的附属品,难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了获得近亲属的证人证言,司法机关采取了鼓励甚至“逼迫”的方法。虽然查明案情很重要,但不应牺牲人伦亲情。真正的司法正义并非只关注案件的最终结果,而是需要全面考虑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同时,长期存在的“大义灭亲”“舍己报国”的思想阻碍了“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尽管舍小取大、大义灭亲的观念值得肯定,但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先天形成,而人们对亲人的爱与保护却是本能反应。[6]如果不平衡这两种价值观,小家的利益可能会损害大家的利益,对两者的发展都不利。
重构:当代审视与实践路径
(一)实体法中的重构
1、明确亲属拒证制度的适用主体
一要明确亲属范围主体。《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可以拒绝出庭作证的近亲属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结合古代法制经验的借鉴,有必要对亲属拒证权的主体界限做出适宜且合理的界定。[7]当前,我国家庭结构不断发生演变,父母离异后跟随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生活,或者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长大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纽带。因此,建议将同居的近亲属纳入亲属拒证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同时,法律拟制的亲子关系,因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深厚情感,其亲密程度并不亚于真实的血缘亲情,因此将父母子女的关系延展至收养关系层面,无疑契合我国社会现状的实际需求。二是需对特殊主体适用特殊手段隐匿亲属犯罪事实的处理办法进行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既作为社会一员具有普通大众的属性,又因承担公共职务而拥有一定的公权力。公职人员如果不涉及使用公权力以及利用公职身份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自然人基于家庭亲情关系为近亲属窝藏、包庇,那么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发落。当然,若是利用公权力或利用公职身份为近亲属罪行打掩护或提供逃脱便利,则必须从严从重处理,因为这样的行为不仅涉嫌包庇、窝藏犯罪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渎职行为,既严重侵犯了法益,违背了我国公权力的人民性立场,也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