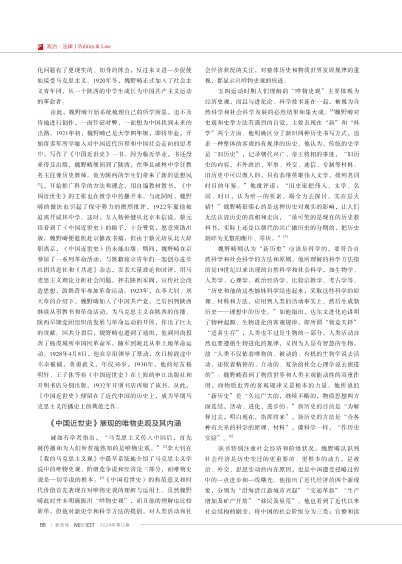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意义
化问题有了更现实的、切身的体会,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魏野畴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个陕西的中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
由此,魏野畴开始系统梳理自己的所学所思,迫不及待地进行创作,一面针砭时弊,一面想为中国找到未来的出路。1921年初,魏野畴已是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开始将多年所学融入对中国近代历程和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中,写作了《中国近世史》一书。因为临近毕业,书还没来得及出版,魏野畴便回到了陕西,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他为陕西的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思想风气,开始推广科学的方法和理念,用自编教材教书,《中国近世史》的主张也在教学中传播开来。与此同时,魏野畴的做法也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批评,1922年夏他被迫离开咸林中学。这时,友人杨钟健从北京来信说,蔡元培看到了《中国近世史》的稿子,十分赞赏,愿意资助出版。魏野畴便趁机赴京修改书稿,但由于蔡元培从北大辞职离京,《中国近世史》仍未能出版。期间,魏野畴在京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陕籍旅京青年们一起创办进步社团共进社和《共进》杂志,发表大量政论和时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抨击陕西军阀,宣传社会改造思想,鼓舞青年参加革命运动。1923年,在李大钊、刘天章的介绍下,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陕西继续从事教书和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与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共分裂后,魏野畴也遭到了通缉,他到河南投奔了杨虎城所率国民革命军,随军到皖北从事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8日,他在阜阳领导了暴动,次日转战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30岁。1930年,他的好友杨明轩、王子休等将《中国近世史》在上海的申江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分别出版,1932年开明书店再版了该书。从此,《中国近世史》便留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中国近世史》展现的唯物史观及其内涵
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是唯物史观。”[2]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最早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论三部分,而唯物史观是一切学说的根本。[3]《中国近世史》的典范意义和时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上。虽然魏野畴此时并未明确提出“唯物史观”,而且他的理解也比较简单,但他对新史学和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关注,对整体历史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重视,都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痕迹。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理解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为经济史观,而且与进化论、科学技术连在一起,被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集大成。[4]魏野畴对史观和史学方法有强烈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新”和“科学”两个方面。他明确区分了新旧两种历史书写方式,追求一种整体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旧历史”,记录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事迹,“旧历史的内容,不外政治、军事、外交、迷信、专制等材料。旧历史中可以傲人的,只有恭维英雄伟人文学,排列名词时日的年鉴。”他批评道:“旧史家把伟人、文学、名词、时日,认为唯一的要素,竭全力去探讨,实在是大错!”魏野畴最痛心的是这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让人们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和走向,“最可笑的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还是以朝代的兴亡做历史的分期的,把历史割碎为无数的断片、零块。”[5]
魏野畴则认为“新历史”应该是科学的,要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指的是19世纪以来出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等。“历史和他的这些姊妹科学结连起来,采取这些科学的原理、材料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的活动事实上,然后生成新历史——理想中的历史。”如他指出,达尔文进化论讲明了物种起源、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也不过是生物的一部分,人类活动自然也要遵循生物进化的规律,又因为人是有智慧的生物,故“人类不仅依着唯物的、被动的、有机的生物学说去活动,还依着精神的、自动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学说去演进的”。魏野畴看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双重作用,而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又是根本的力量。他所说的“新历史”是“久远广大的,继续不断的,物质思想两方面连结,活动、进化、进步的。”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新历史的方法是“合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像科学一样,“作历史实验”。[6]
该书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魏野畴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历史变迁的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动力,是政治、外交、思想变动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遭受侵略过程中的一点进步和一线曙光。他指出了近代经济的四个新现象,分别为“沿海沿江新城市兴起”“交通革新”“生产增加及矿产开放”“移民及垦荒”。他也看到了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剧变,将中国的社会阶级分为三类:官僚和读
由此,魏野畴开始系统梳理自己的所学所思,迫不及待地进行创作,一面针砭时弊,一面想为中国找到未来的出路。1921年初,魏野畴已是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开始将多年所学融入对中国近代历程和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中,写作了《中国近世史》一书。因为临近毕业,书还没来得及出版,魏野畴便回到了陕西,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他为陕西的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思想风气,开始推广科学的方法和理念,用自编教材教书,《中国近世史》的主张也在教学中传播开来。与此同时,魏野畴的做法也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批评,1922年夏他被迫离开咸林中学。这时,友人杨钟健从北京来信说,蔡元培看到了《中国近世史》的稿子,十分赞赏,愿意资助出版。魏野畴便趁机赴京修改书稿,但由于蔡元培从北大辞职离京,《中国近世史》仍未能出版。期间,魏野畴在京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陕籍旅京青年们一起创办进步社团共进社和《共进》杂志,发表大量政论和时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抨击陕西军阀,宣传社会改造思想,鼓舞青年参加革命运动。1923年,在李大钊、刘天章的介绍下,魏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陕西继续从事教书和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与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共分裂后,魏野畴也遭到了通缉,他到河南投奔了杨虎城所率国民革命军,随军到皖北从事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8日,他在阜阳领导了暴动,次日转战途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30岁。1930年,他的好友杨明轩、王子休等将《中国近世史》在上海的申江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分别出版,1932年开明书店再版了该书。从此,《中国近世史》便留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中国近世史》展现的唯物史观及其内涵
诚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是唯物史观。”[2]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最早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论三部分,而唯物史观是一切学说的根本。[3]《中国近世史》的典范意义和时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上。虽然魏野畴此时并未明确提出“唯物史观”,而且他的理解也比较简单,但他对新史学和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关注,对整体历史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重视,都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痕迹。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理解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为经济史观,而且与进化论、科学技术连在一起,被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集大成。[4]魏野畴对史观和史学方法有强烈的自觉,主要表现在“新”和“科学”两个方面。他明确区分了新旧两种历史书写方式,追求一种整体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旧历史”,记录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事迹,“旧历史的内容,不外政治、军事、外交、迷信、专制等材料。旧历史中可以傲人的,只有恭维英雄伟人文学,排列名词时日的年鉴。”他批评道:“旧史家把伟人、文学、名词、时日,认为唯一的要素,竭全力去探讨,实在是大错!”魏野畴最痛心的是这种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让人们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和走向,“最可笑的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还是以朝代的兴亡做历史的分期的,把历史割碎为无数的断片、零块。”[5]
魏野畴则认为“新历史”应该是科学的,要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指的是19世纪以来出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等。“历史和他的这些姊妹科学结连起来,采取这些科学的原理、材料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的活动事实上,然后生成新历史——理想中的历史。”如他指出,达尔文进化论讲明了物种起源、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也不过是生物的一部分,人类活动自然也要遵循生物进化的规律,又因为人是有智慧的生物,故“人类不仅依着唯物的、被动的、有机的生物学说去活动,还依着精神的、自动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学说去演进的”。魏野畴看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双重作用,而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又是根本的力量。他所说的“新历史”是“久远广大的,继续不断的,物质思想两方面连结,活动、进化、进步的。”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新历史的方法是“合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像科学一样,“作历史实验”。[6]
该书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魏野畴认识到社会经济是历史变迁的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动力,是政治、外交、思想变动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遭受侵略过程中的一点进步和一线曙光。他指出了近代经济的四个新现象,分别为“沿海沿江新城市兴起”“交通革新”“生产增加及矿产开放”“移民及垦荒”。他也看到了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剧变,将中国的社会阶级分为三类:官僚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