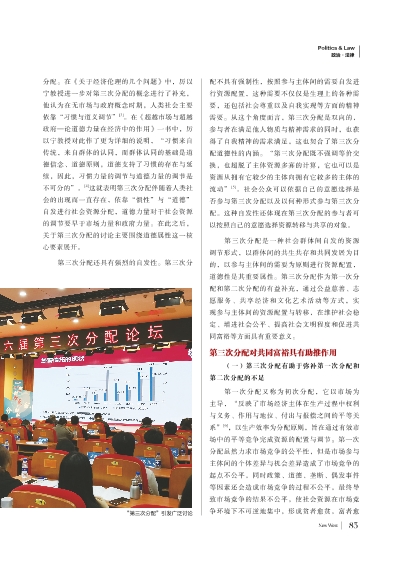韧性治理: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第三次分配”引发广泛讨论
“第三次分配”引发广泛讨论 分配。在《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中,厉以宁教授进一步对第三次分配的概念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在无市场与政府概念时期,人类社会主要依靠“习惯与道义调节”[3]。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厉以宁教授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习惯来自传统,来自群体的认同,而群体认同的基础是道德信念、道德原则,道德支持了习惯的存在与延续,因此,习惯力量的调节与道德力量的调节是不可分的”。[4]这就表明第三次分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一直存在,依靠“惯性”与“道德”自发进行社会资源分配,道德力量对于社会资源的调节要早于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在此之后,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主要围绕道德属性这一核心要素展开。
第三次分配还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第三次分配不具有强制性,按照参与主体间的需要自发进行资源配置,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各种需要,还包括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方面的精神需要。从这个角度而言,第三次分配是双向的,参与者在满足他人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自我精神的需求满足,这也契合了第三次分配道德性的内涵。“第三次分配既不强调等价交换,也超脱了主体资源多寡的计算,它也可以是资源从拥有它较少的主体向拥有它较多的主体的流动”[5]。社会公众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与第三次分配以及以何种形式参与第三次分配。这种自发性还体现在第三次分配的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资源转移与共享的对象。
第三次分配是一种社会群体间自发的资源调节形式,以群体间的共生共存和共同发展为目的,以参与主体间的需要为原则进行资源配置,道德性是其重要属性。第三次分配作为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有益补充,通过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共享经济和文化艺术活动等方式,实现参与主体间的资源配置与转移,在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公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
(一)第三次分配有助于弥补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
第一次分配又称为初次分配,它以市场为主导,“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在生产过程中权利与义务、作用与地位、付出与报偿之间的平等关系”[6],以生产效率为分配原则,旨在通过有效市场中的平等竞争完成资源的配置与调节。第一次分配虽然力求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但是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个体差异与机会差异造成了市场竞争的起点不公平,同时政策、道德、垄断、偶发事件等因素还会造成市场竞争的过程不公平,最终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果不公平,使社会资源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可逆地集中,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