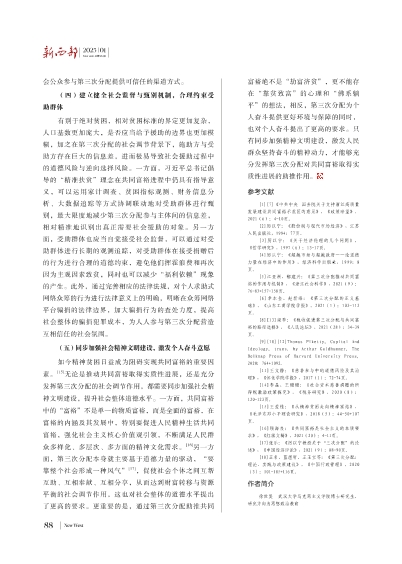韧性治理: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会公众参与第三次分配提供可信任的渠道方式。
(四)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与甄别机制,合理约束受助群体
有别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更加复杂,人口基数更加庞大,是否应当给予援助的边界也更加模糊,加之在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背景下,施助方与受助方存在巨大的信息差,进而极易导致社会援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精准扶贫”理念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仍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运用家计调查、贫困指标观测、财务信息分析、大数据追踪等方式协调联动地对受助群体进行甄别,最大限度地减少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差,相对精准地识别出真正需要社会援助的对象。另一方面,受助群体也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可以通过对受助群体进行长期的观测追踪,对受助群体在接受捐赠后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道德约束,避免他们挥霍浪费和再次因为主观因素致贫,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此外,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个人求助式网络众筹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明晰在众筹网络平台骗捐的法律边界,加大骗捐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社会整体的骗捐犯罪成本,为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营造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
(五)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个人奋斗意愿
如今精神贫困日益成为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15]无论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作用,都需要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一方面,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而是全面的富裕,在富裕的内涵及其发展中,特别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6]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本身就主要基于道德力量的驱动,“要靠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17],促使社会个体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奉献、互相分享,从而达到财富转移与资源平衡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对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能存在“靠贫致富”的心理和“佛系躺平”的想法,相反,第三次分配为个人奋斗提供更好环境与保障的同时,也对个人奋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同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人民群众坚持奋斗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政策瞭望》,2021(6):4-10页。
[2]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7页。
[3]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7(6):13-17页。
[4]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8页。
[5]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157-158页。
[6]李水金、赵新峰:《第三次分配的正义基础》,《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1):103-113页。
[8][13]梁季:《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21(28):34-39页。
[9][10][12]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Ideolog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764+1092.
[11]王文静:《慈善参与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怀化学院学报》,2017(1):72-74页。
[14]李晶、王珊珊:《社会资本慈善捐赠的所得税激励政策探究》,《税务研究》,2020(8):120-123页。
[15]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44-50+107页。
[16]顾海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红旗文稿》,2021(20):4-11页。
[17]张乐:《厉以宁教授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中国经济评论》,2021(9):88-90页。
[18]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5+116页。
作者简介
徐世昊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四)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与甄别机制,合理约束受助群体
有别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更加复杂,人口基数更加庞大,是否应当给予援助的边界也更加模糊,加之在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背景下,施助方与受助方存在巨大的信息差,进而极易导致社会援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精准扶贫”理念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仍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运用家计调查、贫困指标观测、财务信息分析、大数据追踪等方式协调联动地对受助群体进行甄别,最大限度地减少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差,相对精准地识别出真正需要社会援助的对象。另一方面,受助群体也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可以通过对受助群体进行长期的观测追踪,对受助群体在接受捐赠后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道德约束,避免他们挥霍浪费和再次因为主观因素致贫,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此外,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个人求助式网络众筹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明晰在众筹网络平台骗捐的法律边界,加大骗捐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社会整体的骗捐犯罪成本,为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营造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
(五)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个人奋斗意愿
如今精神贫困日益成为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15]无论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调节作用,都需要同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一方面,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而是全面的富裕,在富裕的内涵及其发展中,特别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6]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本身就主要基于道德力量的驱动,“要靠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17],促使社会个体之间互帮互助、互相奉献、互相分享,从而达到财富转移与资源平衡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对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能存在“靠贫致富”的心理和“佛系躺平”的想法,相反,第三次分配为个人奋斗提供更好环境与保障的同时,也对个人奋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同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人民群众坚持奋斗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政策瞭望》,2021(6):4-10页。
[2]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7页。
[3]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7(6):13-17页。
[4]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8页。
[5]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157-158页。
[6]李水金、赵新峰:《第三次分配的正义基础》,《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1):103-113页。
[8][13]梁季:《税收促进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21(28):34-39页。
[9][10][12]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Ideolog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764+1092.
[11]王文静:《慈善参与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怀化学院学报》,2017(1):72-74页。
[14]李晶、王珊珊:《社会资本慈善捐赠的所得税激励政策探究》,《税务研究》,2020(8):120-123页。
[15]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44-50+107页。
[16]顾海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红旗文稿》,2021(20):4-11页。
[17]张乐:《厉以宁教授关于“三次分配”的论述》,《中国经济评论》,2021(9):88-90页。
[18]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5+116页。
作者简介
徐世昊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