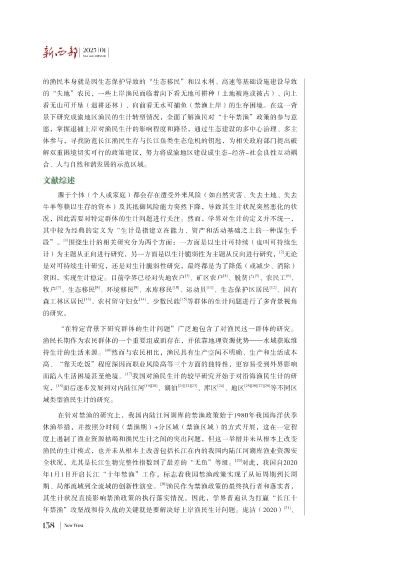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成渝地区上岸渔民生计转型问题研究
的渔民本身就是因生态保护导致的“生态移民”和以水利、高速等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失地”农民,一些上岸渔民面临着向下看无地可耕种(土地被淹或被占)、向上看无山可开垦(退耕还林)、向前看无水可捕鱼(禁渔上岸)的生存困境。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成渝地区渔民的生计转型情况,全面了解渔民对“十年禁渔”政策的参与意愿,掌握退捕上岸对渔民生计的影响程度和路径,通过生态建设的多中心治理、多主体参与,寻找防范长江渔民生存与长江鱼类生态危机的钥匙,为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破解双重困境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努力将成渝地区建设成生态-经济-社会良性互动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示范区域。
文献综述
源于个体(个人或家庭)都会存在遭受外来风险(如自然灾害、失去土地、失去牛羊等赖以生存的资本)及其抵御风险能力突然下降,导致其生计状况突然恶化的状况,因此需要对特定群体的生计问题进行关注。然而,学界对生计的定义并不统一,其中较为经典的定义为“生计是指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谋生手段”。[1]围绕生计的相关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生计可持续(也叫可持续生计)为主题从正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以生计脆弱性为主题从反向进行研究,[2]无论是对可持续生计研究,还是对生计脆弱性研究,最终都是为了降低(或减少、消除)贫困,实现生计稳定。目前学界已经对失地农户[3]、矿区农户[4]、脱贫户[5]、农民工[6]、牧户[7]、生态移民[8]、环境移民[9]、水库移民[10]、运动员[11]、生态保护区居民[12]、国有森工林区居民[13]、农村留守妇女[14]、少数民族[15]等群体的生计问题进行了多背景视角的研究。
“在特定背景下研究群体的生计问题”广泛地包含了对渔民这一群体的研究。渔民长期作为农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而存在,并依靠地理资源优势——水域获取维持生计的生活来源。[16]然而与农民相比,渔民具有生产空间不明确、生产和生活成本高、“靠天吃饭”程度深因而职业风险高等三个方面的独特性,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甚至绝境。[17]我国对渔民生计的较早研究开始于对沿海渔民生计的研究,[18]而后逐步发展到对内陆江河[19][20]、湖泊[21][22][23]、库区[24]、地区[25][26][27][28]等不同区域类型渔民生计的研究。
在针对禁渔的研究上,我国内陆江河湖库的禁渔政策始于1980年我国海洋伏季休渔举措,并按照分时间(禁渔期)+分区域(禁渔区域)的方式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渔业资源枯竭和渔民生计之间的突出问题,但这一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渔民的生计模式,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包括长江在内的我国内陆江河湖库渔业资源安全状况,尤其是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29]对此,我国自2020年1月1日开启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标志着我国禁渔政策实现了从短周期到长周期、局部流域到全流域的创新性演变。[30]渔民作为禁渔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其生计状况直接影响禁渔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打赢“长江十年禁渔”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上岸渔民生计问题。庞洁(2020)[31]、
文献综述
源于个体(个人或家庭)都会存在遭受外来风险(如自然灾害、失去土地、失去牛羊等赖以生存的资本)及其抵御风险能力突然下降,导致其生计状况突然恶化的状况,因此需要对特定群体的生计问题进行关注。然而,学界对生计的定义并不统一,其中较为经典的定义为“生计是指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谋生手段”。[1]围绕生计的相关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生计可持续(也叫可持续生计)为主题从正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以生计脆弱性为主题从反向进行研究,[2]无论是对可持续生计研究,还是对生计脆弱性研究,最终都是为了降低(或减少、消除)贫困,实现生计稳定。目前学界已经对失地农户[3]、矿区农户[4]、脱贫户[5]、农民工[6]、牧户[7]、生态移民[8]、环境移民[9]、水库移民[10]、运动员[11]、生态保护区居民[12]、国有森工林区居民[13]、农村留守妇女[14]、少数民族[15]等群体的生计问题进行了多背景视角的研究。
“在特定背景下研究群体的生计问题”广泛地包含了对渔民这一群体的研究。渔民长期作为农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而存在,并依靠地理资源优势——水域获取维持生计的生活来源。[16]然而与农民相比,渔民具有生产空间不明确、生产和生活成本高、“靠天吃饭”程度深因而职业风险高等三个方面的独特性,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甚至绝境。[17]我国对渔民生计的较早研究开始于对沿海渔民生计的研究,[18]而后逐步发展到对内陆江河[19][20]、湖泊[21][22][23]、库区[24]、地区[25][26][27][28]等不同区域类型渔民生计的研究。
在针对禁渔的研究上,我国内陆江河湖库的禁渔政策始于1980年我国海洋伏季休渔举措,并按照分时间(禁渔期)+分区域(禁渔区域)的方式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渔业资源枯竭和渔民生计之间的突出问题,但这一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渔民的生计模式,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包括长江在内的我国内陆江河湖库渔业资源安全状况,尤其是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29]对此,我国自2020年1月1日开启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标志着我国禁渔政策实现了从短周期到长周期、局部流域到全流域的创新性演变。[30]渔民作为禁渔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其生计状况直接影响禁渔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打赢“长江十年禁渔”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上岸渔民生计问题。庞洁(20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