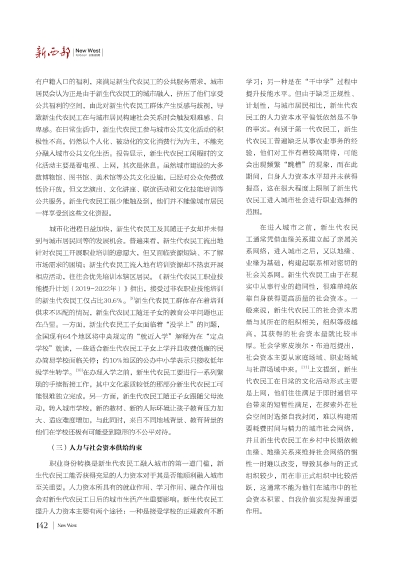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治理变革困境及对策
有户籍人口的福利,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城市居民会认为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挤压了他们享受公共福利的空间,由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产生反感与歧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构建社会关系时会触发艰难感、自卑感。在日常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仍然以个人化、被动化的文化消费行为为主,不能充分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生活。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的文化活动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其次是休息。虽然城市建设的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已经对公众免费或低价开放,但文艺演出、文化讲座、联谊活动和文化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很少能触及到,他们并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这些文化资源。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却并未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普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流出地针对农民工开展职业培训的意愿大,但又面临资源短缺、不了解市场需求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有培训资源却不热衷开展相应活动,往往会优先培训本辖区居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指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比30.6%。[9]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培训供求不匹配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也正在凸显。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面临着“没学上”的问题,全国现有64个地区将中央规定的“就近入学”解释为在“定点学校”就读,一些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上学并且收费低廉的民办简易学校面临关停;约10%地区的公办中小学表示只接收低年级学生转学。[10]在办理入学之前,新生代农民工要进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衔接工作,其中文化素质较低的那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很难独立完成。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跟随父母流动,转入城市学校,新的教材、新的人际环境让孩子教育压力加大、适应难度增加,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地域背景、教育背景的他们在学校还极有可能受到隐形的不公平对待。
(三)人力与社会资本供给约束
职业身份转换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第一道门槛,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获得充足的人力资本对于其是否能顺利融入城市至关重要。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就业作用、学习作用、融合作用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后的城市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种是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不断学习;另一种是在“干中学”过程中提升技能水平。但由于缺乏正规性、计划性,与城市居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依然是不争的事实。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从事农业事务的经验,他们对工作有着较高期待,可能会出现频繁“跳槽”的现象,而在此期间,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却并未获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进行职业选择的范围。
在进入城市之前,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凭借血缘关系建立起了亲属关系网络,进入城市之后,又以地缘、业缘为基础,构建起联系相对密切的社会关系网。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在现实中从事行业的趋同性,很难单纯依靠自身获得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一般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质量与其所在的组织相关,组织等级越高,其获得的社会资本量就比较丰厚。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主要从家庭场域、职业场域与社群场域中来。[11]上文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的文化活动形式主要是上网,他们往往满足于即时通信平台带来的短暂性满足,在探索外在社会空间时选择自我封闭,难以构建需要耗费时间与精力的城市社会网络,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中长期依赖血缘、地缘关系来维持社会网络的惯性一时难以改变,导致其参与的正式组织较少,而在非正式组织中比较活跃,这通常不能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积累、自我价值实现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却并未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普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流出地针对农民工开展职业培训的意愿大,但又面临资源短缺、不了解市场需求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有培训资源却不热衷开展相应活动,往往会优先培训本辖区居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指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比30.6%。[9]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培训供求不匹配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也正在凸显。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面临着“没学上”的问题,全国现有64个地区将中央规定的“就近入学”解释为在“定点学校”就读,一些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上学并且收费低廉的民办简易学校面临关停;约10%地区的公办中小学表示只接收低年级学生转学。[10]在办理入学之前,新生代农民工要进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衔接工作,其中文化素质较低的那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很难独立完成。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跟随父母流动,转入城市学校,新的教材、新的人际环境让孩子教育压力加大、适应难度增加,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地域背景、教育背景的他们在学校还极有可能受到隐形的不公平对待。
(三)人力与社会资本供给约束
职业身份转换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第一道门槛,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获得充足的人力资本对于其是否能顺利融入城市至关重要。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就业作用、学习作用、融合作用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后的城市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种是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不断学习;另一种是在“干中学”过程中提升技能水平。但由于缺乏正规性、计划性,与城市居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依然是不争的事实。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从事农业事务的经验,他们对工作有着较高期待,可能会出现频繁“跳槽”的现象,而在此期间,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却并未获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进行职业选择的范围。
在进入城市之前,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凭借血缘关系建立起了亲属关系网络,进入城市之后,又以地缘、业缘为基础,构建起联系相对密切的社会关系网。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在现实中从事行业的趋同性,很难单纯依靠自身获得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一般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质量与其所在的组织相关,组织等级越高,其获得的社会资本量就比较丰厚。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主要从家庭场域、职业场域与社群场域中来。[11]上文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的文化活动形式主要是上网,他们往往满足于即时通信平台带来的短暂性满足,在探索外在社会空间时选择自我封闭,难以构建需要耗费时间与精力的城市社会网络,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中长期依赖血缘、地缘关系来维持社会网络的惯性一时难以改变,导致其参与的正式组织较少,而在非正式组织中比较活跃,这通常不能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积累、自我价值实现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