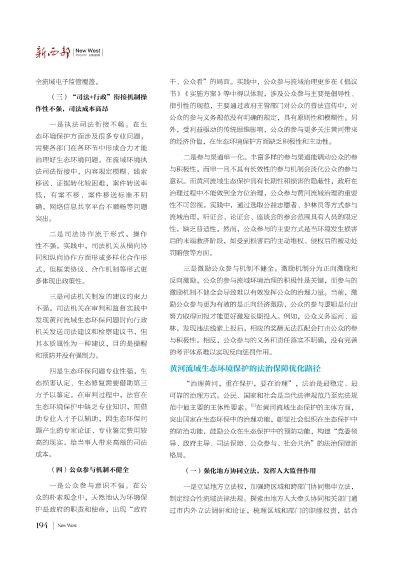鄂尔多斯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法治保障研究
全流域电子监管覆盖。
(三)“司法+行政”衔接机制操作性不强,司法成本高昂
一是执法司法衔接不畅。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涉及很多专业问题,需要各部门在各环节中形成合力才能治理好生态环境问题。在流域环境执法司法衔接中,内容规定模糊、线索移送、证据转化较困难,案件转送率低,有案不移、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网络信息共享平台不顺畅等问题突出。
二是司法协作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司法机关从横向协同和纵向协作方面形成多样化合作形式,但框架协议、合作机制等形式更多体现出政策性。
三是司法机关制发的建议约束力不强。司法机关在审判和监督实践中发现黄河流域生态环保问题时向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书,但其本质属性为一种建议,目的是提醒和预防并没有强制力。
四是生态环保问题专业性强,生态损害认定、生态修复需要借助第三方予以鉴定。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专业知识,需借助专业人才予以辅助,因生态环保问题产生的专家论证、专业鉴定费用较高的现实,给当事人带来高额的司法成本。
(四)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
一是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在公众的朴素观念中,天然地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职责和使命,出现“政府干、公众看”的局面。实践中,公众参与流域治理更多在《倡议书》《实施方案》等中得以体现,涉及公众参与主要是倡导性、指引性的规范,主要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对公众的普法宣传中,对公众的参与义务规范没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另外,受利益驱动的传统思维影响,公众的参与更多关注黄河带来的经济价值,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参与渠道单一化。丰富多样的参与渠道能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而单一且不具有长效性的参与机制会淡化公众的参与意识。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长期性和损害的隐蔽性,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能做到全方位治理,公众参与黄河流域治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实践中,通过选取公益志愿者、护林员等方式参与流域治理,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的参会范围具有人员的限定性,缺乏普适性。然而,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是当环境发生损害后的末端救济阶段,如受到损害后的主动维权、侵权后的被动处罚赔偿等方面。
三是激励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公众的参与流域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是关键,而参与的激励机制不健全会导致难以有效发挥公众的治理力量。当前,激励公众参与更为有效的是正向经济激励,公众的参与逻辑是付出努力取得回报才能更好激发长期投入。例如,公众义务巡河、巡林,发现违法线索上报后,相应的奖酬无法匹配会打击公众的参与积极性。相反,公众参与的义务和责任落实不明确,没有完善的考评体系难以实现反向惩罚作用。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优化路径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法治是最稳定、最可靠的治理方式。公民、国家和社会是当代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中最主要的主体性要素。[2]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主体方面,突出国家在生态环保中的治理功能,彰显社会组织在生态保护中的防治功能,鼓励公众在生态保护中的预防功能,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司法保障、公众参与、社会共治”的法治保障新格局。
(一)强化地方协同立法,发挥人大监督作用
一是立足地方立法权,加强跨区域和跨部门协同集中立法,制定综合性流域法律法规。探索由地方人大牵头协同相关部门通过市内外立法调研和论证,梳理区域和部门的职能权责,结合
(三)“司法+行政”衔接机制操作性不强,司法成本高昂
一是执法司法衔接不畅。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涉及很多专业问题,需要各部门在各环节中形成合力才能治理好生态环境问题。在流域环境执法司法衔接中,内容规定模糊、线索移送、证据转化较困难,案件转送率低,有案不移、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网络信息共享平台不顺畅等问题突出。
二是司法协作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司法机关从横向协同和纵向协作方面形成多样化合作形式,但框架协议、合作机制等形式更多体现出政策性。
三是司法机关制发的建议约束力不强。司法机关在审判和监督实践中发现黄河流域生态环保问题时向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书,但其本质属性为一种建议,目的是提醒和预防并没有强制力。
四是生态环保问题专业性强,生态损害认定、生态修复需要借助第三方予以鉴定。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专业知识,需借助专业人才予以辅助,因生态环保问题产生的专家论证、专业鉴定费用较高的现实,给当事人带来高额的司法成本。
(四)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
一是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在公众的朴素观念中,天然地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职责和使命,出现“政府干、公众看”的局面。实践中,公众参与流域治理更多在《倡议书》《实施方案》等中得以体现,涉及公众参与主要是倡导性、指引性的规范,主要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对公众的普法宣传中,对公众的参与义务规范没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另外,受利益驱动的传统思维影响,公众的参与更多关注黄河带来的经济价值,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参与渠道单一化。丰富多样的参与渠道能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而单一且不具有长效性的参与机制会淡化公众的参与意识。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长期性和损害的隐蔽性,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能做到全方位治理,公众参与黄河流域治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实践中,通过选取公益志愿者、护林员等方式参与流域治理,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的参会范围具有人员的限定性,缺乏普适性。然而,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是当环境发生损害后的末端救济阶段,如受到损害后的主动维权、侵权后的被动处罚赔偿等方面。
三是激励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公众的参与流域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是关键,而参与的激励机制不健全会导致难以有效发挥公众的治理力量。当前,激励公众参与更为有效的是正向经济激励,公众的参与逻辑是付出努力取得回报才能更好激发长期投入。例如,公众义务巡河、巡林,发现违法线索上报后,相应的奖酬无法匹配会打击公众的参与积极性。相反,公众参与的义务和责任落实不明确,没有完善的考评体系难以实现反向惩罚作用。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优化路径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法治是最稳定、最可靠的治理方式。公民、国家和社会是当代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中最主要的主体性要素。[2]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主体方面,突出国家在生态环保中的治理功能,彰显社会组织在生态保护中的防治功能,鼓励公众在生态保护中的预防功能,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司法保障、公众参与、社会共治”的法治保障新格局。
(一)强化地方协同立法,发挥人大监督作用
一是立足地方立法权,加强跨区域和跨部门协同集中立法,制定综合性流域法律法规。探索由地方人大牵头协同相关部门通过市内外立法调研和论证,梳理区域和部门的职能权责,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