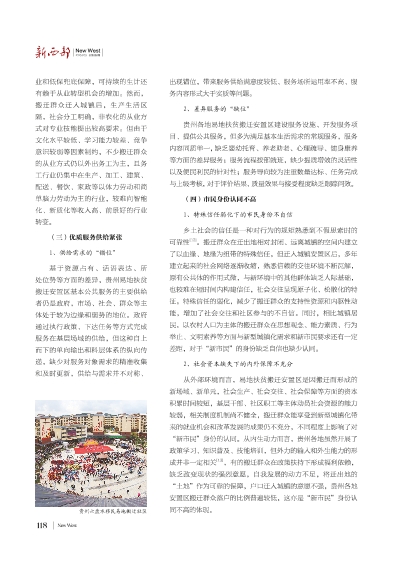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贵州六盘水移民易地搬迁社区
业和低保兜底保障,可持续的生计还有赖于从业转型机会的增加。然而,搬迁群众迁入城镇后,生产生活区隔,社会分工明确,非农化的从业方式对专业技能提出较高要求。但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竞争意识较弱等因素制约,不少搬迁群众的从业方式仍以外出务工为主,且务工行业仍集中在生产、加工、建筑、配送、餐饮、家政等以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为主的行业,较难向智能化、新质化等收入高、前景好的行业转变。(三)优质服务供给紧张1、 供给需求的“错位”
基于资源占有、话语表达、所处位势等方面的差异,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仍是政府,市场、社会、群众等主体处于较为边缘和弱势的地位。政府通过执行政策、下达任务等方式完成服务在基层场域的供给,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输出和科层体系的纵向传递,缺少对服务对象需求的精准收集和及时更新,供给与需求并不对称、出现错位,带来服务供给满意度较低、服务场所运用率不高、服务内容形式大于实质等问题。
2、差异服务的“缺位”
贵州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建设服务设施、开发服务项目、提供公共服务,但多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常规服务,服务内容同质单一,缺乏婴幼托育、养老助老、心理疏导、健身康养等方面的差异服务;服务流程按部就班,缺少提质增效的灵活性以及便民利民的针对性;服务导向较为注重数量达标、任务完成与上级考核,对于评价结果、质量效果与接受程度缺乏跟踪问效。(四)市民身份认同不高1、特殊信任弱化下的市民身份不自信乡土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对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12]可靠性 。搬迁群众在迁出地相对封闭、远离城镇的空间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特殊信任,但迁入城镇安置区后,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逐渐收缩,熟悉信赖的交往环境不断瓦解,原有公共体的作用式微,与新环境中的其他群体缺乏人际基础,也较难在短时间内构建信任,社会交往呈现原子化、松散化的特征。特殊信任的弱化,减少了搬迁群众的支持性资源和内驱性动能,增加了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的不自信。同时,相比城镇居民,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搬迁群众在思想观念、能力素质、行为举止、文明素养等方面与新型城镇化需求和新市民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对于“新市民”的身份缺乏自信也缺少认同。
2、社会资本缺失下的内外保障不充分
从外部环境而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是因搬迁而形成的新场域、新单元,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本积累时间较短,基层干部、社区职工等主体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弱,相关制度机制尚不健全,搬迁群众能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改革发展的成果仍不充分,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 新市民”身份的认同。从内生动力而言,贵州各地虽然开展了政策学习、知识普及、技能培训,但外力的输入和外生能力的形成并非一定相关 ,有的搬迁群众在政策扶持下形成福利依赖,
[13 ]缺乏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自我发展的动力不足,将迁出地的“ 土地”作为可靠的保障,户口迁入城镇的意愿不强,贵州各地安置区搬迁群众落户的比例普遍较低,这亦是“新市民”身份认同不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