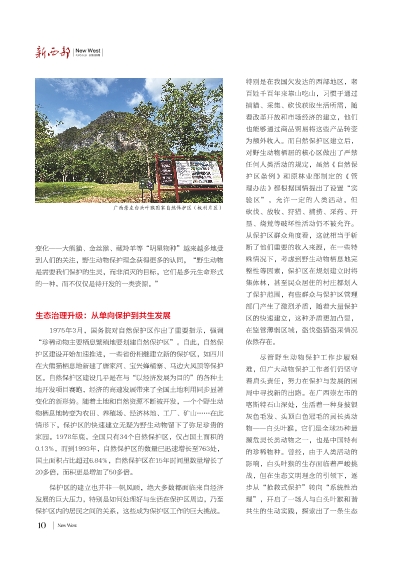人类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 冲突与共生的生态叙事

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自然保护区(板利片区)
变化——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等“明星物种”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理念获得更多的认同,“野生动物是需要我们保护的生灵,而非消灭的目标,它们是多元生命形式的一种,而不仅仅是待开发的一类资源。 ”
生态治理升级:从单向保护到共生发展
1975年3月,国务院对自然保护区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 珍稀动物主要栖息繁殖地要划建自然保护区”。自此,自然保护区建设开始加速推进,一些省份相继建立新的保护区,如四川在大熊猫栖息地新建了唐家河、宝兴蜂桶寨、马边大风顶等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建设几乎是在与“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各种土地开发项目赛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国土地利用同步显著变化的新形势。随着土地和自然资源不断被开发,一个个野生动物栖息地转变为农田、养殖场、经济林地、工厂、矿山……在此情形下,保护区的快速建立无疑为野生动物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家园。1978年底,全国只有34个自然保护区,仅占国土面积的0.13% ,而到1993年,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已迅速增长至763处,国土面积占比超过6.84%,自然保护区在15年时间里数量增长了20多倍,面积更是增加了50多倍。
保护区的建立也并非一帆风顺,绝大多数都面临来自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与生活在保护区周边,乃至保护区内的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成为保护区工作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在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老百姓千百年来靠山吃山,习惯于通过捕猎、采集、砍伐获取生活所需,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他们也能够通过商品贸易将这些产品转变为额外收入。而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对野生动物栖居的核心区做出了严禁任何人类活动的规定,虽然《自然保护区条例》和原林业部制定的《管理办法》都根据国情提出了设置“实验区”,允许一定的人类活动,但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等破坏性活动仍不被允许。从保护区群众角度看,这就相当于斩断了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考虑到野生动物栖息地完整性等因素,保护区在规划建立时将集体林,甚至民众居住的村庄都划入了保护范围,有些群众与保护区管理部门产生了激烈矛盾,随着大量保护区的快速建立,这种矛盾更加凸显,在监管薄弱区域,盗伐盗猎盗采情况依然存在。
尽管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步履艰难,但广大动物保护工作者们仍坚守着肩头责任,努力在保护与发展的困局中寻找新的出路。在广西崇左市的喀斯特石山深处,生活着一种身披银灰色毛发、头顶白色冠毛的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它们是全球25种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曾经,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白头叶猴的生存面临着严峻挑战,但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下,逐步从“抢救式保护”转向“系统性治理”,开启了一场人与白头叶猴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