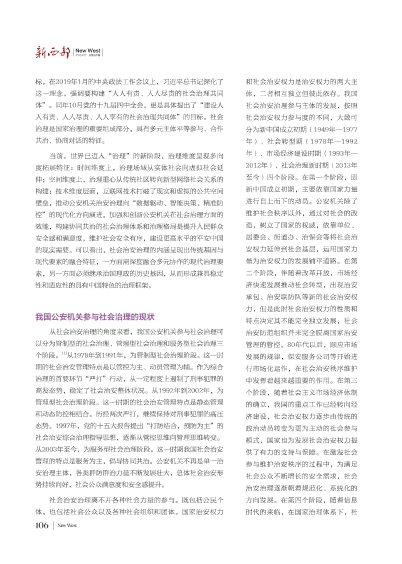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对策及展望
标。在2019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化了这一理念,强调要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具体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合作共治、协商对话的特征。
当前,世界已迈入“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维度呈现多向度拓展特征:时间维度上,治理场域从实体社会向虚拟社会延伸;空间维度上,治理重心从传统社区转向新型网络社会关系的构建;技术维度层面,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现实和虚拟的公共空间壁垒,推动公安机关治安治理向“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精准防控”的现代化方向演进。加强和创新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效能,构建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是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维护社会安全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现实需要。可以看出,社会治安治理的内涵呈现出传统基因与现代要素的融合特征,一方面需深度融合多元协作的现代治理要素,另一方面必须继承治国理政的历史基因,从而形成兼具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
我国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可以分为管制型的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和服务型社会治理三个阶段。[1] 从1978年到1991年,为管制型社会治理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管理特点是以管控为主、动员管理为辅。作为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严打”行动,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刑事犯罪的高发态势,稳定了社会治安整体状况。从1992年到2002年,为管理型社会治理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管理特点是静态管理和动态防控相结合。历经两次严打,继续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思想,逐渐从管控思维向管理思维转变。从2003年至今,为服务型社会治理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的特点是服务为主,倡导协同共治。公安机关不再是单一治安治理主体,各类群防群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总体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社会公众满意度和安全感提升。
社会治安治理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既包括公民个体,也包括社会公众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国家治安权力和社会治安权力是治安权力的两大主体,二者相互独立但彼此依存。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参与主体的发展,按照社会治安权力参与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 1977年)、社会转型期(1978年— 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时期(1993年—2012年)、社会治理新时期(2013年至今)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依靠国家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公安机关除了维护社会秩序以外,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树立了国家的权威,依靠单位、居委会、街道办、治保会等将社会治安权力延伸到社会基层,运用国家力量为治安权力的发展铺平道路。在第二个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转型,出现治安承包、治安联防队等新的社会治安权力,但是此时社会治安权力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不能完全独立发展,社会治安防范组织并未完全脱离国家治安管理的管控。80年代以后,顺应市场发展的规律,保安服务公司等开始进行市场化运作,在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第三个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重点工作已经转向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权力逐步由传统的政治动员转变为更为主动的社会参与模式,国家也为发展社会治安权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在激发社会参与维护治安秩序的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逐渐朝着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在第四个阶段,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社
当前,世界已迈入“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维度呈现多向度拓展特征:时间维度上,治理场域从实体社会向虚拟社会延伸;空间维度上,治理重心从传统社区转向新型网络社会关系的构建;技术维度层面,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现实和虚拟的公共空间壁垒,推动公安机关治安治理向“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精准防控”的现代化方向演进。加强和创新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效能,构建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是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维护社会安全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现实需要。可以看出,社会治安治理的内涵呈现出传统基因与现代要素的融合特征,一方面需深度融合多元协作的现代治理要素,另一方面必须继承治国理政的历史基因,从而形成兼具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
我国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可以分为管制型的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和服务型社会治理三个阶段。[1] 从1978年到1991年,为管制型社会治理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管理特点是以管控为主、动员管理为辅。作为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严打”行动,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刑事犯罪的高发态势,稳定了社会治安整体状况。从1992年到2002年,为管理型社会治理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管理特点是静态管理和动态防控相结合。历经两次严打,继续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思想,逐渐从管控思维向管理思维转变。从2003年至今,为服务型社会治理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管理的特点是服务为主,倡导协同共治。公安机关不再是单一治安治理主体,各类群防群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总体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社会公众满意度和安全感提升。
社会治安治理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既包括公民个体,也包括社会公众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国家治安权力和社会治安权力是治安权力的两大主体,二者相互独立但彼此依存。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参与主体的发展,按照社会治安权力参与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 1977年)、社会转型期(1978年— 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时期(1993年—2012年)、社会治理新时期(2013年至今)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依靠国家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公安机关除了维护社会秩序以外,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树立了国家的权威,依靠单位、居委会、街道办、治保会等将社会治安权力延伸到社会基层,运用国家力量为治安权力的发展铺平道路。在第二个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转型,出现治安承包、治安联防队等新的社会治安权力,但是此时社会治安权力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不能完全独立发展,社会治安防范组织并未完全脱离国家治安管理的管控。80年代以后,顺应市场发展的规律,保安服务公司等开始进行市场化运作,在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第三个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重点工作已经转向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权力逐步由传统的政治动员转变为更为主动的社会参与模式,国家也为发展社会治安权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在激发社会参与维护治安秩序的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逐渐朝着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在第四个阶段,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