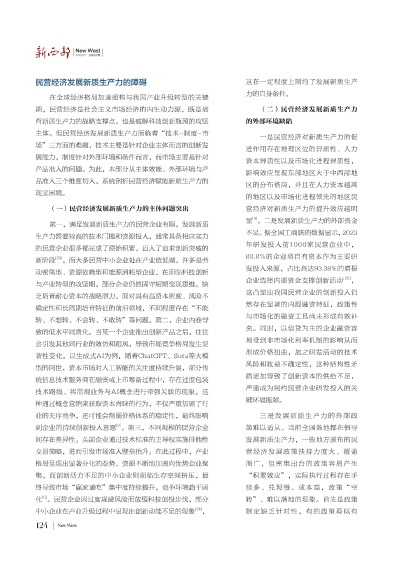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路径研究
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障碍
在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与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源,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点,也是破解科技创新瓶颈的攻坚主体。但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着“技术-制度-市场”三方面的难题,技术主要是针对企业主体而言的创新发展能力,制度针对外部环境和条件而言,而市场主要是针对产品准入的问题。为此,本部分从主体效能、外部环境与产品准入三个维度切入,系统剖析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
(一)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问题突出
第一,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民营企业有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较高的技术门槛和资源投入,通常具备相应实力的民营企业很多都完成了原始积累,迈入了追求创新突破的新阶段[20],而大多民营中小企业处在产业链低端,许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和能源消耗型企业,在面临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的攻坚期,部分企业仍然固守短期变现思维,缺乏培育耐心资本的战略潜力,面对具有高资本密度、风险不确定性和长周期培育特征的前沿领域,不同程度存在“不能转、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第二,企业内卷导致的低水平同质化。当某一个企业推出创新产品之后,往往会引发其他同行业的效仿和跟风,导致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显著性变化。以生成式AI为例,随着ChatGPT、Sora等大模型的问世,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部分传统信息技术服务商在融资或上市筹备过程中,存在过度包装技术路线、将常规业务与AI概念进行牵强关联的现象。这种通过概念营销来获取资本青睐的行为,不仅严重加剧了行业的无序竞争,还可能会削弱价格体系的稳定性,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持续创新投入意愿 。第三,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间存在差异性。[ 8]头部企业通过技术标准的主导权实施排他性交易策略,进而引发市场准入壁垒抬升。在此过程中,产业格局呈现出显著分化的态势,资源不断地加速向优势企业聚集,而创新活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则面临生存空间挤压,最终导致市场“赢家通吃”集中度持续提升,竞争环境趋于固化[6]。民营企业因过度规避风险而放缓科技创投步伐,部分中小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呈现出创新动能不足的现象 ,[24]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自身条件。
( 二)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外部环境缺陷
一是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存在地理区位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异质性以及市场化进程异质性,影响效应呈现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分布格局,并且在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以及市场化进程领先的地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越明显 。[4]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外部资金不足。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2023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中,88.8%的企业将自有资本作为主要研发投入来源,占比高达93.38%的填报 企业选择内部资金支撑创新活动[25 ] ,这凸显出我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仍然存在显著的内源融资特征,政策性与市场化的融资工具尚未形成有效补充。同时,以信贷为主的企业融资容易受到非市场化利率机制的影响从而形成价格扭曲,加之研发活动的技术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这种结构性矛盾更加导致了创新资本的供给不足,严重成为制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关键环境瓶颈。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外部政策难以适从。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些地方颁布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力度大、覆盖面广,但密集出台的政策容易产生“积累效应”,实际执行过程存在手续多、兑现慢、成本高,政策“空转”、难以落地的现象。首先是政策制定缺乏针对性,有的政策看似有
在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与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源,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点,也是破解科技创新瓶颈的攻坚主体。但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着“技术-制度-市场”三方面的难题,技术主要是针对企业主体而言的创新发展能力,制度针对外部环境和条件而言,而市场主要是针对产品准入的问题。为此,本部分从主体效能、外部环境与产品准入三个维度切入,系统剖析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
(一)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问题突出
第一,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民营企业有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较高的技术门槛和资源投入,通常具备相应实力的民营企业很多都完成了原始积累,迈入了追求创新突破的新阶段[20],而大多民营中小企业处在产业链低端,许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和能源消耗型企业,在面临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的攻坚期,部分企业仍然固守短期变现思维,缺乏培育耐心资本的战略潜力,面对具有高资本密度、风险不确定性和长周期培育特征的前沿领域,不同程度存在“不能转、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第二,企业内卷导致的低水平同质化。当某一个企业推出创新产品之后,往往会引发其他同行业的效仿和跟风,导致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显著性变化。以生成式AI为例,随着ChatGPT、Sora等大模型的问世,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部分传统信息技术服务商在融资或上市筹备过程中,存在过度包装技术路线、将常规业务与AI概念进行牵强关联的现象。这种通过概念营销来获取资本青睐的行为,不仅严重加剧了行业的无序竞争,还可能会削弱价格体系的稳定性,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持续创新投入意愿 。第三,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间存在差异性。[ 8]头部企业通过技术标准的主导权实施排他性交易策略,进而引发市场准入壁垒抬升。在此过程中,产业格局呈现出显著分化的态势,资源不断地加速向优势企业聚集,而创新活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则面临生存空间挤压,最终导致市场“赢家通吃”集中度持续提升,竞争环境趋于固化[6]。民营企业因过度规避风险而放缓科技创投步伐,部分中小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呈现出创新动能不足的现象 ,[24]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自身条件。
( 二)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外部环境缺陷
一是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存在地理区位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异质性以及市场化进程异质性,影响效应呈现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分布格局,并且在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以及市场化进程领先的地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越明显 。[4]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外部资金不足。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2023年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中,88.8%的企业将自有资本作为主要研发投入来源,占比高达93.38%的填报 企业选择内部资金支撑创新活动[25 ] ,这凸显出我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仍然存在显著的内源融资特征,政策性与市场化的融资工具尚未形成有效补充。同时,以信贷为主的企业融资容易受到非市场化利率机制的影响从而形成价格扭曲,加之研发活动的技术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这种结构性矛盾更加导致了创新资本的供给不足,严重成为制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关键环境瓶颈。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外部政策难以适从。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些地方颁布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力度大、覆盖面广,但密集出台的政策容易产生“积累效应”,实际执行过程存在手续多、兑现慢、成本高,政策“空转”、难以落地的现象。首先是政策制定缺乏针对性,有的政策看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