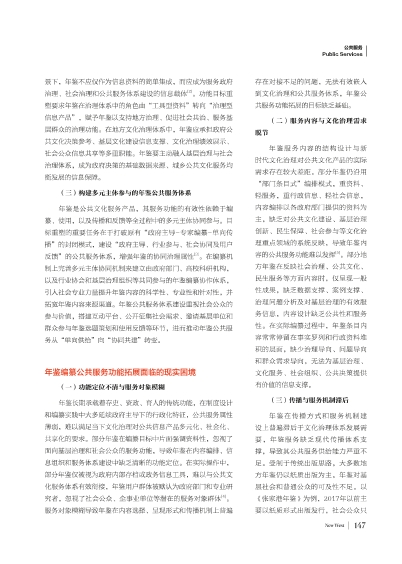文化治理视域下 年鉴编纂的公共服务功能拓展研究
景下,年鉴不应仅作为信息资料的简单集成,而应成为服务政府[2]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信息载体 。功能目标重塑要求年鉴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由“工具型资料”转向“治理型信息产品”,赋予年鉴以支持地方治理、促进社会共治、服务基层群众的治理功能。在地方文化治理体系中,年鉴应承担政府公共文化决策参考、基层文化建设信息支撑、文化治理绩效展示、社会公众信息共享等多重职能。年鉴要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成为政府决策的基础数据来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信息保障。
(三)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年鉴公共服务体系
年鉴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其服务功能的有效性依赖于编纂、使用,以及传播和反馈等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目标重塑的重要任务在于打破原有“政府主导-专家编纂-单向传播”的封闭模式,建设“政府主导、行业参与、社会协同及用户反馈”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年鉴的协同治理属性 。 [3] 在编纂机制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来建立由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和基层治理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年鉴编纂协作体系,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提升年鉴内容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并拓宽年鉴内容来源渠道。年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价值,搭建互动平台、公开征集社会需求、邀请基层单位和群众参与年鉴选题策划和使用反馈等环节,进而推动年鉴公共服务从“单向供给”向“协同共建”转变。
年鉴编纂公共服务功能拓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功能定位不清与服务对象模糊
年鉴长期承载着存史、资政、育人的传统功能,在制度设计和编纂实践中大多延续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化特征,公共服务属性薄弱,难以满足当下文化治理对公共信息产品多元化、社会化、共享化的要求。部分年鉴在编纂目标中片面强调资料性,忽视了面向基层治理和社会公众的服务功能,导致年鉴在内容编排、信息组织和服务体系建设中缺乏清晰的功能定位。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年鉴仅被视为政府内部存档或政务信息工具,难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衔接,年鉴用户群体被默认为政府部门和专业研究者,忽视了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等潜在的服务对象群体[4]。服务对象模糊导致年鉴在内容选择、呈现形式和传播机制上普遍存在对接不足的问题,无法有效嵌入到文化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年鉴公共服务功能拓展的目标缺乏基础。
( 二)服务内容与文化治理需求脱节
年鉴服务内容的结构设计与新时代文化治理对公共文化产品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年鉴仍沿用“ 部门条目式”编排模式,重资料、轻服务,重行政信息、轻社会信息,内容编排以各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主,缺乏对公共文化建设、基层治理创新、民生保障、社会参与等文化治理重点领域的系统反映,导致年鉴内容的公共服务功能难以发挥 。[5] 部分地方年鉴在反映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民生服务等方面内容时,仅呈现一般性成果,缺乏数据支撑、案例支撑、治理问题分析及对基层治理的有效服务信息,内容设计缺乏公共性和服务性。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年鉴条目内容常常停留在事实罗列和行政资料堆积的层面,缺少治理导向、问题导向和群众需求导向,无法为基层治理、文化服务、社会组织、公共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支撑。
(三)传播与服务机制滞后
年鉴在传播方式和服务机制建设上普遍滞后于文化治理体系发展需要,年鉴服务缺乏现代传播体系支撑,导致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受制于传统出版思路,大多数地方年鉴仍以纸质出版为主,年鉴对基层社会和普通公众的可及性不足。以《张家港年鉴》为例,2017年以前主要以纸质形式出版发行,社会公众只
(三)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年鉴公共服务体系
年鉴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其服务功能的有效性依赖于编纂、使用,以及传播和反馈等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目标重塑的重要任务在于打破原有“政府主导-专家编纂-单向传播”的封闭模式,建设“政府主导、行业参与、社会协同及用户反馈”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年鉴的协同治理属性 。 [3] 在编纂机制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来建立由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和基层治理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年鉴编纂协作体系,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提升年鉴内容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并拓宽年鉴内容来源渠道。年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价值,搭建互动平台、公开征集社会需求、邀请基层单位和群众参与年鉴选题策划和使用反馈等环节,进而推动年鉴公共服务从“单向供给”向“协同共建”转变。
年鉴编纂公共服务功能拓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功能定位不清与服务对象模糊
年鉴长期承载着存史、资政、育人的传统功能,在制度设计和编纂实践中大多延续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化特征,公共服务属性薄弱,难以满足当下文化治理对公共信息产品多元化、社会化、共享化的要求。部分年鉴在编纂目标中片面强调资料性,忽视了面向基层治理和社会公众的服务功能,导致年鉴在内容编排、信息组织和服务体系建设中缺乏清晰的功能定位。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年鉴仅被视为政府内部存档或政务信息工具,难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衔接,年鉴用户群体被默认为政府部门和专业研究者,忽视了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等潜在的服务对象群体[4]。服务对象模糊导致年鉴在内容选择、呈现形式和传播机制上普遍存在对接不足的问题,无法有效嵌入到文化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年鉴公共服务功能拓展的目标缺乏基础。
( 二)服务内容与文化治理需求脱节
年鉴服务内容的结构设计与新时代文化治理对公共文化产品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年鉴仍沿用“ 部门条目式”编排模式,重资料、轻服务,重行政信息、轻社会信息,内容编排以各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主,缺乏对公共文化建设、基层治理创新、民生保障、社会参与等文化治理重点领域的系统反映,导致年鉴内容的公共服务功能难以发挥 。[5] 部分地方年鉴在反映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民生服务等方面内容时,仅呈现一般性成果,缺乏数据支撑、案例支撑、治理问题分析及对基层治理的有效服务信息,内容设计缺乏公共性和服务性。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年鉴条目内容常常停留在事实罗列和行政资料堆积的层面,缺少治理导向、问题导向和群众需求导向,无法为基层治理、文化服务、社会组织、公共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支撑。
(三)传播与服务机制滞后
年鉴在传播方式和服务机制建设上普遍滞后于文化治理体系发展需要,年鉴服务缺乏现代传播体系支撑,导致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受制于传统出版思路,大多数地方年鉴仍以纸质出版为主,年鉴对基层社会和普通公众的可及性不足。以《张家港年鉴》为例,2017年以前主要以纸质形式出版发行,社会公众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