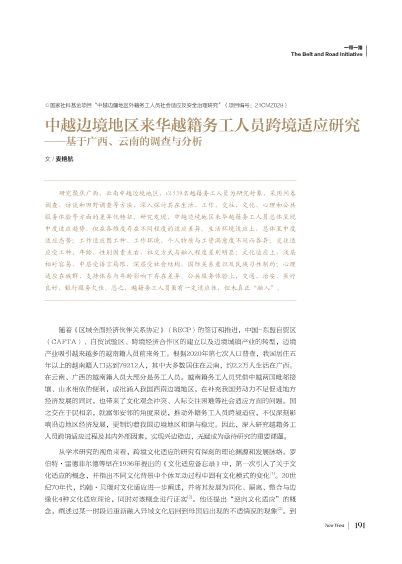中越边境地区来华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研究— —基于广西、云南的调查与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越边疆地区外籍务工人员社会适应及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 21CMZ028)
研究聚焦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以539名越籍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法,深入探讨其在生活、工作、交往、文化、心理和公共服务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研究发现,中越边境地区来华越籍务工人员总体呈现中度适应趋势,但在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差异。生活环境适应上,总体呈中度适应态势;工作适应因工种、工作环境、个人特质与工资满意度不同而各异;交往适应受工种、年龄、性别因素左右,社交方式与融入程度差别明显;文化适应上,浅层相对容易,中层受语言局限,深层受社会结构、国际关系意识及民族习性制约;心理适应在族群、支持体系与年龄影响下存在差异。公共服务体验上,交通、治安、医疗良好,银行服务欠佳。总之,越籍务工人员虽有一定适应性,但未真正“融入” 。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的签订和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CA FTA) 、自贸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以及边境城镇产业的转型,边境产业吸引越来越多的越南籍人员前来务工。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居住五年以上的越南籍人口达到79212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云南,约2.2万人生活在广西。在云南、广西的越南籍人员大部分是务工人员。越南籍务工人员凭借中越两国毗邻接壤、山水相依的便利,成批涌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在补充我国劳动力不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观念冲突、人际交往困难等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就富邻安邻的角度来说,推动外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不仅深刻影响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更制约着我国边境地区和谐与稳定。因此,深入研究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过程及其内外部因素,实现兴边稳边,无疑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跨境文化适应的研究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等早在1936年提出的《文化适应备忘录》中,第一次引入了关于文化适应的概念,并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互动过程中固有文化模式的变化[1]。 20世纪70年代,约翰·贝瑞对文化适应进一步阐述,并将其发展为同化、隔离、整合与边缘化4种文化适应理论,同时对该概念进行证实 。[2]他还提出“逆向文化适应”的概念,阐述过某一时段后重新融入异域文化后回到母国后出现的不适情况的现象[3 ]。到
研究聚焦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以539名越籍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法,深入探讨其在生活、工作、交往、文化、心理和公共服务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研究发现,中越边境地区来华越籍务工人员总体呈现中度适应趋势,但在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差异。生活环境适应上,总体呈中度适应态势;工作适应因工种、工作环境、个人特质与工资满意度不同而各异;交往适应受工种、年龄、性别因素左右,社交方式与融入程度差别明显;文化适应上,浅层相对容易,中层受语言局限,深层受社会结构、国际关系意识及民族习性制约;心理适应在族群、支持体系与年龄影响下存在差异。公共服务体验上,交通、治安、医疗良好,银行服务欠佳。总之,越籍务工人员虽有一定适应性,但未真正“融入” 。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的签订和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CA FTA) 、自贸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以及边境城镇产业的转型,边境产业吸引越来越多的越南籍人员前来务工。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居住五年以上的越南籍人口达到79212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云南,约2.2万人生活在广西。在云南、广西的越南籍人员大部分是务工人员。越南籍务工人员凭借中越两国毗邻接壤、山水相依的便利,成批涌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在补充我国劳动力不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观念冲突、人际交往困难等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就富邻安邻的角度来说,推动外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不仅深刻影响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更制约着我国边境地区和谐与稳定。因此,深入研究越籍务工人员跨境适应过程及其内外部因素,实现兴边稳边,无疑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跨境文化适应的研究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等早在1936年提出的《文化适应备忘录》中,第一次引入了关于文化适应的概念,并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互动过程中固有文化模式的变化[1]。 20世纪70年代,约翰·贝瑞对文化适应进一步阐述,并将其发展为同化、隔离、整合与边缘化4种文化适应理论,同时对该概念进行证实 。[2]他还提出“逆向文化适应”的概念,阐述过某一时段后重新融入异域文化后回到母国后出现的不适情况的现象[3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