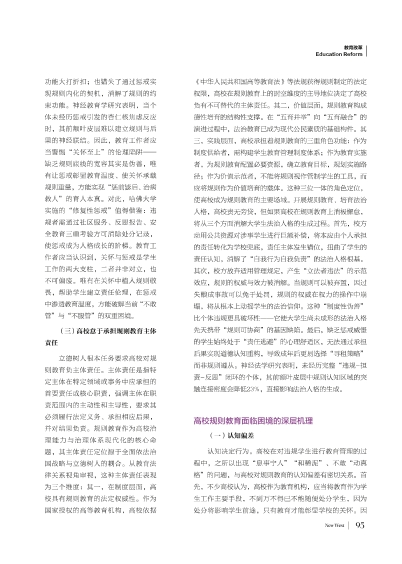高校规则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以典型个案为例
功能大打折扣;也错失了通过惩戒实现规则内化的契机,消解了规则的约束功能。神经教育学研究表明,当个体未经历惩戒引发的杏仁核焦虑反应时,其前额叶皮层难以建立规则与后果的神经联结。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当警惕“关怀至上”的伦理陷阱— —缺乏规则底线的宽容其实是伪善,唯有让惩戒彰显教育温度、使关怀承载规则重量,方能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育人本真。对此,哈佛大学实施的“修复性惩戒”值得借鉴:违规者需通过社区服务、反思报告、安全教育三重考验方可消除处分记录,使惩戒成为人格成长的阶梯。教育工作者应当认识到,关怀与惩戒是学生工作的两大支柱,二者并非对立,也不可偏废。唯有在关怀中植入规则敬畏,帮助学生建立责任伦理,在惩戒中渗透教育温度,方能破解当前“不敢管”与“不服管”的双重困境。
(三)高校怠于承担规则教育主体责任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高校对规则教育负主体责任。主体责任是指特定主体在特定领域或事务中应承担的首要责任或核心职责,强调主体在职责范围内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要求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相应后果,并对结果负责。规则教育作为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其主体责任定位源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与立德树人的耦合。从教育法律关系视角审视,这种主体责任表现为三个维度:其一,在制度层面,高校具有规则教育的法定权威性。作为国家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规获得规则制定的法定权限,高校在规则教育上的时空维度的主导地位决定了高校负有不可替代的主体责任。其二,价值层面,规则教育构成德性培育的结构性支撑。在“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的演进过程中,法治教育已成为现代公民素质的基础构件。其三,实践层面,高校承担着规则教育的三重角色功能:作为制度供给者,需构建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体系;作为教育实施者,为规则教育配置必要资源,确立教育目标,规划实施路径;作为价值示范者,不能将规则视作管制学生的工具,而应将规则作为价值培育的载体。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定位,使高校成为规则教育的主要场域。开展规则教育、培育法治人格,高校责无旁贷,但如果高校在规则教育上消极懈怠,将从三个方面消解大学生法治人格的生成过程。首先,校方动用公共资源对涉事学生进行巨额补偿,将本应由个人承担的责任转化为学校兜底,责任主体发生错位,扭曲了学生的责任认知,消解了“自我行为自我负责”的法治人格根基。其次,校方放弃适用管理规定,产生“立法者违法”的示范效应,规则的权威与效力被消解。当规则可以被弃置,因过失酿成事故可以免于处罚,规则的权威在权力的操作中崩塌,将从根本上动摇学生的法治信仰。这种“制度性伪善”比个体违规更具破坏性——它使大学生尚未成形的法治人格先天携带“规则可协商”的基因缺陷。最后,缺乏惩戒威慑的学生始终处于“责任逃避”的心理舒适区,无法通过承担后果实现道德认知重构,导致成年后更易选择“寻租策略”而非规则遵从。神经法学研究表明,未经历完整“违规-担责-反思”闭环的个体,其前额叶皮层中规则认知区域的突触连接密度会降低23%,直接影响法治人格的生成。
高校规则教育面临困境的深层机理
(一)认知偏差
认知决定行为。高校在对违规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息事宁人”“和稀泥”、不敢“动真格”的问题,与高校对规则教育的认知偏差有密切关系。首先,不少高校认为,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应当将教育作为学生工作主要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处分学生,因为处分将影响学生前途,只有教育才能彰显学校的关怀。因
(三)高校怠于承担规则教育主体责任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高校对规则教育负主体责任。主体责任是指特定主体在特定领域或事务中应承担的首要责任或核心职责,强调主体在职责范围内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要求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相应后果,并对结果负责。规则教育作为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其主体责任定位源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与立德树人的耦合。从教育法律关系视角审视,这种主体责任表现为三个维度:其一,在制度层面,高校具有规则教育的法定权威性。作为国家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规获得规则制定的法定权限,高校在规则教育上的时空维度的主导地位决定了高校负有不可替代的主体责任。其二,价值层面,规则教育构成德性培育的结构性支撑。在“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的演进过程中,法治教育已成为现代公民素质的基础构件。其三,实践层面,高校承担着规则教育的三重角色功能:作为制度供给者,需构建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体系;作为教育实施者,为规则教育配置必要资源,确立教育目标,规划实施路径;作为价值示范者,不能将规则视作管制学生的工具,而应将规则作为价值培育的载体。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定位,使高校成为规则教育的主要场域。开展规则教育、培育法治人格,高校责无旁贷,但如果高校在规则教育上消极懈怠,将从三个方面消解大学生法治人格的生成过程。首先,校方动用公共资源对涉事学生进行巨额补偿,将本应由个人承担的责任转化为学校兜底,责任主体发生错位,扭曲了学生的责任认知,消解了“自我行为自我负责”的法治人格根基。其次,校方放弃适用管理规定,产生“立法者违法”的示范效应,规则的权威与效力被消解。当规则可以被弃置,因过失酿成事故可以免于处罚,规则的权威在权力的操作中崩塌,将从根本上动摇学生的法治信仰。这种“制度性伪善”比个体违规更具破坏性——它使大学生尚未成形的法治人格先天携带“规则可协商”的基因缺陷。最后,缺乏惩戒威慑的学生始终处于“责任逃避”的心理舒适区,无法通过承担后果实现道德认知重构,导致成年后更易选择“寻租策略”而非规则遵从。神经法学研究表明,未经历完整“违规-担责-反思”闭环的个体,其前额叶皮层中规则认知区域的突触连接密度会降低23%,直接影响法治人格的生成。
高校规则教育面临困境的深层机理
(一)认知偏差
认知决定行为。高校在对违规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息事宁人”“和稀泥”、不敢“动真格”的问题,与高校对规则教育的认知偏差有密切关系。首先,不少高校认为,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应当将教育作为学生工作主要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处分学生,因为处分将影响学生前途,只有教育才能彰显学校的关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