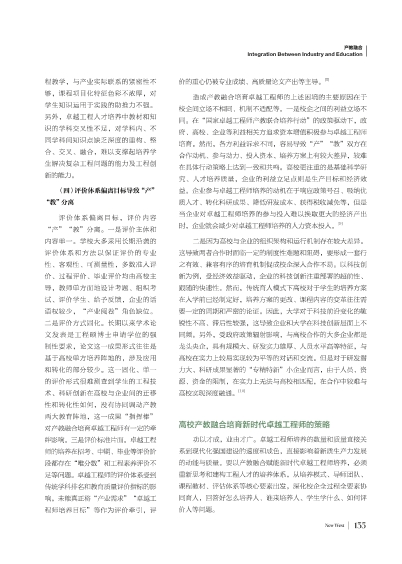产教融合培育新时代卓越工程师的路径探索
程教学,与产业实际联系的紧密性不够,课程项目化特征色彩不浓厚,对学生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助推力不强。另外,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中教材和知识的学科交叉性不足,对学科内、不同学科间知识点缺乏深度的重构、整合、交叉、融合,难以支撑起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及工程创新的能力。
(四)评价体系偏离目标导致“产”“教”分离
评价体系偏离目标,评价内容“产”“教”分离。一是评价主体和内容单一。学校大多采用长期沿袭的评价体系和方法以保证评价的专业性、客观性、可测量性,多数准入评价、过程评价、毕业评价均由高校主导,教师单方面地设计考题、组织考试、评价学生、给予反馈,企业的话语权较少,“产业阅卷”角色缺位。二是评价方式固化。长期以来学术论文发表是工程硕博士申请学位的强制性要求,论文这一成果形式往往是基于高校单方培养阵地的,涉及应用和转化的部分较少。这一固化、单一的评价形式很难测查到学生的工程技术、科研创新在高校与企业间的迁移性和转化性如何,没有协同调动产教两大教育阵地,这一成果“指挥棒”对产教融合培育卓越工程师有一定的牵绊影响。三是评价标准片面。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招考、中期、毕业等评价阶段都存在“唯分数”和工程素养评价不足等问题。卓越工程师的评价体系受到传统学科排名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影响,未能真正将“产业需求”“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等作为评价牵引,评价的重心仍被专业成绩、高质量论文产出等主导。[8]
造成产教融合培育卓越工程师的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校企间立场不相同、机制不适配等。一是校企之间的利益立场不同。在“国家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行动”的政策驱动下,政府、高校、企业等利益相关方追求资本增值积极参与卓越工程师培育。然而,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容易导致“产”“教”双方在合作动机、参与动力、投入资本、培养方案上有较大差异,较难在具体行动策略上达到一致和共鸣。高校更注重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质量,企业的利益立足点则是生产目标和经济效益。企业参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动机在于响应政策号召、吸纳优质人才、转化科研成果、降低研发成本、获得税收减免等,但是当企业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参与投入难以换取更大的经济产出时,企业就会减少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人力资本投入。[9]
二是因为高校与企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两者合作时面临一定的制度性难题和阻碍,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兼容有序的培育机制促成校企深入合作不易。以科技创新为例,受经济效益驱动,企业的科技创新注重部署的超前性、跟随的快速性。然而,传统育人模式下高校对于学生的培养方案在入学前已经制定好,培养方案的更改、课程内容的变革往往需要一定的周期和严密的论证。因此,大学对于科技前沿变化的敏锐性不高、滞后性较强,这导致企业和大学在科技创新层面上不同频。另外,受政府政策辐射影响,与高校合作的大多企业都是龙头央企,具有规模大、研发实力雄厚、人员水平高等特征,与高校在实力上较易实现较为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但是对于研发潜力大、科研成果显著的“专精特新”小企业而言,由于人员、资源、资金的限制,在实力上无法与高校相匹配,在合作中较难与高校实现深度融通。[10]
高校产教融合培育新时代卓越工程师的策略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速度和成色,直接影响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能与质量。要以产教融合赋能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必须重新思考和建构工程人才的培养体系,从培养模式、导师团队、课程教材、评估体系等核心要素出发,深化校企全过程全要素协同育人,回答好怎么培养人、谁来培养人、学生学什么、如何评价人等问题。
(四)评价体系偏离目标导致“产”“教”分离
评价体系偏离目标,评价内容“产”“教”分离。一是评价主体和内容单一。学校大多采用长期沿袭的评价体系和方法以保证评价的专业性、客观性、可测量性,多数准入评价、过程评价、毕业评价均由高校主导,教师单方面地设计考题、组织考试、评价学生、给予反馈,企业的话语权较少,“产业阅卷”角色缺位。二是评价方式固化。长期以来学术论文发表是工程硕博士申请学位的强制性要求,论文这一成果形式往往是基于高校单方培养阵地的,涉及应用和转化的部分较少。这一固化、单一的评价形式很难测查到学生的工程技术、科研创新在高校与企业间的迁移性和转化性如何,没有协同调动产教两大教育阵地,这一成果“指挥棒”对产教融合培育卓越工程师有一定的牵绊影响。三是评价标准片面。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招考、中期、毕业等评价阶段都存在“唯分数”和工程素养评价不足等问题。卓越工程师的评价体系受到传统学科排名和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影响,未能真正将“产业需求”“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等作为评价牵引,评价的重心仍被专业成绩、高质量论文产出等主导。[8]
造成产教融合培育卓越工程师的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校企间立场不相同、机制不适配等。一是校企之间的利益立场不同。在“国家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行动”的政策驱动下,政府、高校、企业等利益相关方追求资本增值积极参与卓越工程师培育。然而,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容易导致“产”“教”双方在合作动机、参与动力、投入资本、培养方案上有较大差异,较难在具体行动策略上达到一致和共鸣。高校更注重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质量,企业的利益立足点则是生产目标和经济效益。企业参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动机在于响应政策号召、吸纳优质人才、转化科研成果、降低研发成本、获得税收减免等,但是当企业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参与投入难以换取更大的经济产出时,企业就会减少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人力资本投入。[9]
二是因为高校与企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两者合作时面临一定的制度性难题和阻碍,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兼容有序的培育机制促成校企深入合作不易。以科技创新为例,受经济效益驱动,企业的科技创新注重部署的超前性、跟随的快速性。然而,传统育人模式下高校对于学生的培养方案在入学前已经制定好,培养方案的更改、课程内容的变革往往需要一定的周期和严密的论证。因此,大学对于科技前沿变化的敏锐性不高、滞后性较强,这导致企业和大学在科技创新层面上不同频。另外,受政府政策辐射影响,与高校合作的大多企业都是龙头央企,具有规模大、研发实力雄厚、人员水平高等特征,与高校在实力上较易实现较为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但是对于研发潜力大、科研成果显著的“专精特新”小企业而言,由于人员、资源、资金的限制,在实力上无法与高校相匹配,在合作中较难与高校实现深度融通。[10]
高校产教融合培育新时代卓越工程师的策略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速度和成色,直接影响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能与质量。要以产教融合赋能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必须重新思考和建构工程人才的培养体系,从培养模式、导师团队、课程教材、评估体系等核心要素出发,深化校企全过程全要素协同育人,回答好怎么培养人、谁来培养人、学生学什么、如何评价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