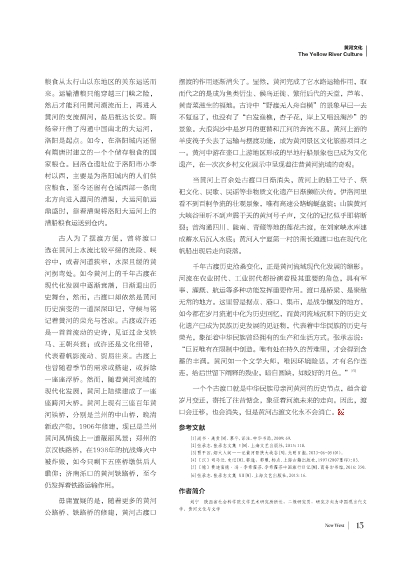千年舟楫处,黄河古渡口
粮食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关东运送而来。运输漕粮只能穿越三门峡之险,然后才能利用黄河溯流而上,再进入黄河的支流渭河,最后抵达长安。隋炀帝开凿了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洛阳是起点。如今,在洛阳城内还留有隋唐时建立的一个个储存粮食的国家粮仓。回洛仓遗址位于洛阳市小李村以西,主要是为洛阳城内的人们供应粮食,至今还留有仓城西部一条南北方向进入瀍河的漕渠,大运河航运鼎盛时,靠着漕渠将洛阳大运河上的漕船粮食运送到仓内。
古人为了摆渡方便,曾将渡口选在黄河上水流比较平缓的流段、峡谷中,或者河道狭窄,水深且缓的黄河拐弯处。如今黄河上的千年古渡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渐衰落,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古渡口却依然是黄河历史演变的一道深深印记,守候与铭记着黄河的荣光与苍凉。古渡或许还是一首首流动的史诗,见证过金戈铁马、王朝兴衰;或许还是文化纽带,代表着帆影流动、贸易往来。古渡上也曾随着季节的需求或搭建,或拆除一座座浮桥。然而,随着黄河流域的现代化发展,黄河上陆续建成了一座座跨河大桥。黄河上现有三座百年黄河铁桥,分别是兰州的中山桥,晚清新政产物,1906年修建,现已是兰州黄河风情线上一道靓丽风景;郑州的京汉铁路桥,在1938年的抗战烽火中被炸毁,如今只剩下五座桥墩供后人瞻仰;济南泺口的黄河铁路桥,至今仍发挥着铁路运输作用。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更多的黄河公路桥、铁路桥的修建,黄河古渡口摆渡的作用逐渐消失了。显然,黄河完成了它水路运输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成为鱼类衍生、候鸟迁徙、繁衍后代的天堂,芦苇、黄青菜滋生的福地。古诗中“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也没有了“白发渔樵,杏子花,岸上又唱浪淘沙”的景象。大浪淘沙中是岁月的更替和江河的奔流不息。黄河上游的羊皮筏子失去了运输与摆渡功能,成为黄河景区文化旅游项目之一。黄河中游在壶口上游地区形成的旱地行船景象也已成为文化遗产,在一次次乡村文化展示中呈现着往昔黄河流域的奇观。
当黄河上百余处古渡口日渐消失,黄河上的船工号子、祭祀文化、民歌、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濒临失传。伊洛河里看不到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唯有高速公路蜿蜒盘旋;山陕黄河大峡谷里听不到声震于天的黄河号子声,文化的记忆似乎即将断裂;曾沟通四川、陇南、青藏等地的莲花古渡,在刘家峡水库建成蓄水后沉入水底;黄河入宁夏第一村的南长滩渡口也在现代化帆船出现后走向衰落。
千年古渡历史沧桑变化,正是黄河流域现代化发展的缩影。河流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具有军事、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发挥重要作用。渡口是桥梁、是聚散无常的地方。这里曾是据点、港口、集市,是战争爆发的地方,如今都在岁月流逝中化为历史回忆,而黄河流域沉积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物,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荣光,象征着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张承志说:“巨匠唯有在限制中创造。唯有处在持久的苦难里,才会得到含蓄的丰满。黄河如一个文学大师,唯因环境险恶,才有名作连连,给后世留下阐释的残业,暗自圆缺,如姣好的月色。 ”[6]
一个个古渡口就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历史节点,蕴含着岁月变迁,寄托了往昔惦念,象征着河流未来的走向。因此,渡口会迁移,也会消失,但是黄河古渡文化永不会消亡。
参考文献
[1]尚书·禹贡[M].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69.[2]张承志.张承志文集 V[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18.[3]贾平凹.烟火人间——记黄河晋陕大峡谷[N].光明日报,2023-06-05(01).[4]〔 汉〕司马迁.史记[M].郭逸、郭曼,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7重印):83.[5]〔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M].商务印书馆,2016:350.[6]张承志.张承志文集 XⅡ[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6.
作者简介
刘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黄河文化与文学
古人为了摆渡方便,曾将渡口选在黄河上水流比较平缓的流段、峡谷中,或者河道狭窄,水深且缓的黄河拐弯处。如今黄河上的千年古渡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渐衰落,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古渡口却依然是黄河历史演变的一道深深印记,守候与铭记着黄河的荣光与苍凉。古渡或许还是一首首流动的史诗,见证过金戈铁马、王朝兴衰;或许还是文化纽带,代表着帆影流动、贸易往来。古渡上也曾随着季节的需求或搭建,或拆除一座座浮桥。然而,随着黄河流域的现代化发展,黄河上陆续建成了一座座跨河大桥。黄河上现有三座百年黄河铁桥,分别是兰州的中山桥,晚清新政产物,1906年修建,现已是兰州黄河风情线上一道靓丽风景;郑州的京汉铁路桥,在1938年的抗战烽火中被炸毁,如今只剩下五座桥墩供后人瞻仰;济南泺口的黄河铁路桥,至今仍发挥着铁路运输作用。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更多的黄河公路桥、铁路桥的修建,黄河古渡口摆渡的作用逐渐消失了。显然,黄河完成了它水路运输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成为鱼类衍生、候鸟迁徙、繁衍后代的天堂,芦苇、黄青菜滋生的福地。古诗中“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也没有了“白发渔樵,杏子花,岸上又唱浪淘沙”的景象。大浪淘沙中是岁月的更替和江河的奔流不息。黄河上游的羊皮筏子失去了运输与摆渡功能,成为黄河景区文化旅游项目之一。黄河中游在壶口上游地区形成的旱地行船景象也已成为文化遗产,在一次次乡村文化展示中呈现着往昔黄河流域的奇观。
当黄河上百余处古渡口日渐消失,黄河上的船工号子、祭祀文化、民歌、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濒临失传。伊洛河里看不到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唯有高速公路蜿蜒盘旋;山陕黄河大峡谷里听不到声震于天的黄河号子声,文化的记忆似乎即将断裂;曾沟通四川、陇南、青藏等地的莲花古渡,在刘家峡水库建成蓄水后沉入水底;黄河入宁夏第一村的南长滩渡口也在现代化帆船出现后走向衰落。
千年古渡历史沧桑变化,正是黄河流域现代化发展的缩影。河流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具有军事、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发挥重要作用。渡口是桥梁、是聚散无常的地方。这里曾是据点、港口、集市,是战争爆发的地方,如今都在岁月流逝中化为历史回忆,而黄河流域沉积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物,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荣光,象征着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张承志说:“巨匠唯有在限制中创造。唯有处在持久的苦难里,才会得到含蓄的丰满。黄河如一个文学大师,唯因环境险恶,才有名作连连,给后世留下阐释的残业,暗自圆缺,如姣好的月色。 ”[6]
一个个古渡口就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历史节点,蕴含着岁月变迁,寄托了往昔惦念,象征着河流未来的走向。因此,渡口会迁移,也会消失,但是黄河古渡文化永不会消亡。
参考文献
[1]尚书·禹贡[M].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69.[2]张承志.张承志文集 V[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18.[3]贾平凹.烟火人间——记黄河晋陕大峡谷[N].光明日报,2023-06-05(01).[4]〔 汉〕司马迁.史记[M].郭逸、郭曼,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7重印):83.[5]〔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M].商务印书馆,2016:350.[6]张承志.张承志文集 XⅡ[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6.
作者简介
刘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黄河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