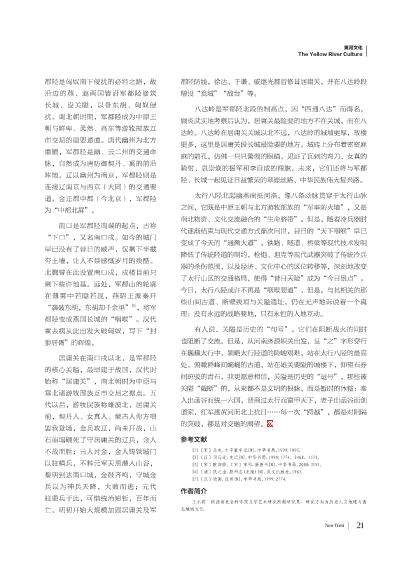太行八陉:穿越千年的文明走廊
都陉是匈奴南下侵扰的必经之路,故沿边的燕、赵两国皆沿军都陉修筑长城、设关隘,以备东胡、匈奴侵扰。南北朝时期,军都陉成为中原王朝与鲜卑、柔然、高车等游牧部族互市交易的重要通道。唐代幽州为北方重镇,军都陉是幽、云二州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唐防御契丹、奚的前沿阵地。辽以幽州为南京,军都陉则是连接辽南京与西京(大同)的交通要道。金迁都中都(今北京),军都陉为“中都北屏” 。
南口是军都陉南端的起点,古称“下口”,又名南口戍。如今的城门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严,仅剩下半截夯土墙,让人不禁感慨岁月的残酷。北魏曾在此设置南口戍,戍楼目前只剩下些许地基。远处,军都山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燕昭王派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5],将军都陉变成燕国长城的“咽喉”。汉代霍去病从此出发大破匈奴,写下“封狼居胥”的辉煌。
居庸关在南口戍以北,是军都陉的核心关隘,最早建于战国,汉代时始称“居庸关”,南北朝时为中原与塞北诸游牧部族互市交易之据点。五代以后,游牧民族称雄漠北,居庸关前,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你方唱罢我登场,金兵攻辽,尚未开战,山石崩塌砸死了守居庸关的辽兵,金人不战而胜;元人讨金,金人铸铁城门以驻精兵,不料元军天黑潜入山谷,黎明到达南口城,金鼓齐鸣,守城金兵以为神兵天降,大败而逃;元代驻重兵于此,可惜统治短暂,百年而亡。明初开始大规模加固居庸关及军都陉防线,徐达、于谦、戚继光都曾修葺居庸关,并在八达岭段增设“瓮城”“敌台”等。
八达岭是军都陉北段的制高点,因“四通八达”而得名,顾炎武实地考察后认为,居庸关最险要的地方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八达岭在居庸关关城以北不远,八达岭的城墙更厚,敌楼更多,这里是居庸关段长城最险要的地方。城砖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箭孔,仿佛一只只警惕的眼睛,见证了瓦剌的弯刀、女真的骑射、袁崇焕的援军和李自成的闯旗,未来,它们还将与军都陉、长城一起见证日益繁荣的草原丝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
太行八陉北起幽燕南抵河洛,像八条动脉贯穿于太行山脉之间,它既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军事防火墙”,又是南北物资、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命脐带”。但是,随着冷兵器时代逐渐结束与现代交通方式渐次问世,昔日的“天下咽喉”早已变成了今天的“通衢大道”,铁路、隧道、桥梁等现代技术发明降低了传统陉道的制约,枪炮、坦克等现代武器突破了传统冷兵器的杀伤范围,以及经济、文化中心的区位转移等,深刻地改变了太行山区的交通格局,使得“昔日天险”成为“今日景点” 。今日,太行八陉或许不再是“咽喉要道”,但是,与其相关的那些山间古道、断壁残垣与关隘遗址,仍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真理:没有永远的战略要地,只有永恒的人地互动。
有人说,关隘是历史的“句号”,它们在阻断战火的同时也阻断了交流。但是,从河南济源轵关出发,呈“之”字形穿行在巍巍太行中,领略太行陉道的险峻艰难,站在太行八陉的最高处,俯瞰群峰间蜿蜒的古道,站在雄关要隘的城楼下,仰望石券间斑驳的青石,我更愿意相信,关隘是历史的“逗号”,那些被关隘“截断”的,从来都不是文明的根脉,而是暂时的休整:秦人出函谷而统一六国,晋商过太行而富甲天下,老子出函谷而创道家,红军渡黄河而北上抗日……每一次“跨越”,都是对阻隔的突破,都是对交融的渴望。
参考文献
[1]〔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中华书局,1999:1092.[2]〔 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1774、 2468、 1551.[3]〔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2000:3191.[4]〔 清〕庆之金.蔚州志(光绪)[M].成文出版社,1965.[5]〔 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2774.
作者简介
王永莉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与西北地域文化
南口是军都陉南端的起点,古称“下口”,又名南口戍。如今的城门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严,仅剩下半截夯土墙,让人不禁感慨岁月的残酷。北魏曾在此设置南口戍,戍楼目前只剩下些许地基。远处,军都山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燕昭王派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5],将军都陉变成燕国长城的“咽喉”。汉代霍去病从此出发大破匈奴,写下“封狼居胥”的辉煌。
居庸关在南口戍以北,是军都陉的核心关隘,最早建于战国,汉代时始称“居庸关”,南北朝时为中原与塞北诸游牧部族互市交易之据点。五代以后,游牧民族称雄漠北,居庸关前,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你方唱罢我登场,金兵攻辽,尚未开战,山石崩塌砸死了守居庸关的辽兵,金人不战而胜;元人讨金,金人铸铁城门以驻精兵,不料元军天黑潜入山谷,黎明到达南口城,金鼓齐鸣,守城金兵以为神兵天降,大败而逃;元代驻重兵于此,可惜统治短暂,百年而亡。明初开始大规模加固居庸关及军都陉防线,徐达、于谦、戚继光都曾修葺居庸关,并在八达岭段增设“瓮城”“敌台”等。
八达岭是军都陉北段的制高点,因“四通八达”而得名,顾炎武实地考察后认为,居庸关最险要的地方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八达岭在居庸关关城以北不远,八达岭的城墙更厚,敌楼更多,这里是居庸关段长城最险要的地方。城砖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箭孔,仿佛一只只警惕的眼睛,见证了瓦剌的弯刀、女真的骑射、袁崇焕的援军和李自成的闯旗,未来,它们还将与军都陉、长城一起见证日益繁荣的草原丝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
太行八陉北起幽燕南抵河洛,像八条动脉贯穿于太行山脉之间,它既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军事防火墙”,又是南北物资、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命脐带”。但是,随着冷兵器时代逐渐结束与现代交通方式渐次问世,昔日的“天下咽喉”早已变成了今天的“通衢大道”,铁路、隧道、桥梁等现代技术发明降低了传统陉道的制约,枪炮、坦克等现代武器突破了传统冷兵器的杀伤范围,以及经济、文化中心的区位转移等,深刻地改变了太行山区的交通格局,使得“昔日天险”成为“今日景点” 。今日,太行八陉或许不再是“咽喉要道”,但是,与其相关的那些山间古道、断壁残垣与关隘遗址,仍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真理:没有永远的战略要地,只有永恒的人地互动。
有人说,关隘是历史的“句号”,它们在阻断战火的同时也阻断了交流。但是,从河南济源轵关出发,呈“之”字形穿行在巍巍太行中,领略太行陉道的险峻艰难,站在太行八陉的最高处,俯瞰群峰间蜿蜒的古道,站在雄关要隘的城楼下,仰望石券间斑驳的青石,我更愿意相信,关隘是历史的“逗号”,那些被关隘“截断”的,从来都不是文明的根脉,而是暂时的休整:秦人出函谷而统一六国,晋商过太行而富甲天下,老子出函谷而创道家,红军渡黄河而北上抗日……每一次“跨越”,都是对阻隔的突破,都是对交融的渴望。
参考文献
[1]〔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中华书局,1999:1092.[2]〔 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1774、 2468、 1551.[3]〔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2000:3191.[4]〔 清〕庆之金.蔚州志(光绪)[M].成文出版社,1965.[5]〔 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2774.
作者简介
王永莉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与西北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