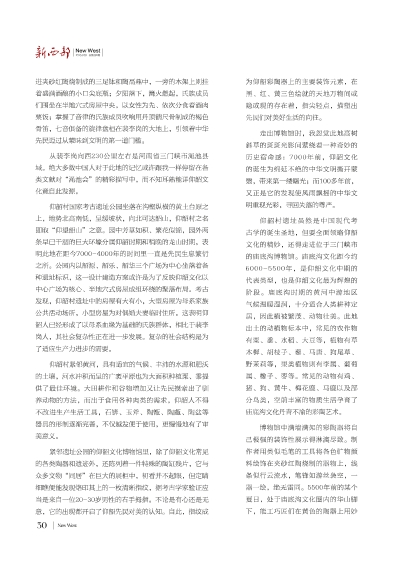黄河岸边的华夏序章
进夹砂红陶烧制成的三足钵和陶鬲鼎中,一旁的木架上则挂着盛满酒酿的小口尖底瓶;夕阳落下,篝火燃起,氏族成员们围坐在半地穴式房屋中央,以女性为先、依次分食着酒肉粟饭;掌握了音律的氏族成员吹响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褐色骨笛,七音俱备的旋律盘桓在裴李岗的大地上,引领着中华先民迈过从蒙昧到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从裴李岗向西230公里左右是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此地的记忆或许跟我一样停留在各类文献对“渑池会”的精彩描写中,而不知耳熟能详仰韶文化竟自此发源。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坐落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原之上,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向北可达韶山,仰韶村之名即取“仰望韶山”之意。园中芳草如积、繁花似锦,园外两条早已干涸的巨大环壕分属仰韶时期和稍晚的龙山时期,表明此地在距今7000-4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先民生息繁衍之所。公园内以韶源、韶乐、韶华三个广场为中心坐落着各种遗址标识,这一设计建造方案或许是为了反映仰韶文化以中心广场为核心、半地穴式房屋成组环绕的聚落布局。考古发现,仰韶村遗址中的房屋有大有小,大型房屋为母系家族公共活动场所,小型房屋为对偶婚夫妻临时住所。这表明仰韶人已经形成了以母系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群体,相比于裴李岗人,其社会复杂性正在进一步发展。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进步的需要。
仰韶村紧邻黄河,具有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河水冲积而呈的广袤平原也为大面积种植粟、黍提供了最佳环境。大田耕作和谷物增加又让先民摸索出了驯养动物的方法,而出于食用各种肉类的需求,仰韶人不得不改进生产生活工具,石锛、玉斧、陶甑、陶甗、陶盆等器具的形制逐渐完善,不仅越发便于使用,更慢慢地有了审美意义。
紧邻遗址公园的仰韶文化博物馆里,除了仰韶文化常见的各类陶器和遗迹外,还陈列着一件特殊的陶缸残片,它与众多文物“同居”在巨大的展柜中,初看并不起眼,但定睛细瞧便能发现烙印其上的一枚清晰指纹,据考古学家验证应当是来自一位20-30岁男性的右手拇指。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它的出现都开启了仰韶先民对美的认知。自此,指纹成为仰韶彩陶器上的主要装饰元素,在黑、红、黄三色绘就的天地万物间或隐或现的存在着,指尖轻点,描塑出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博物馆时,我忽觉此地高树斜草的斑斑光影间萦绕着一种奇妙的历史宿命感: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诞生为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撕开蒙翳,带来第一缕曙光;而100多年前,又正是它的发现使风雨飘摇的中华文明重现光彩,寻回失落的尊严。
仰韶村遗址虽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圣地,但要全面领略仰韶文化的精妙,还得走进位于三门峡市的庙底沟博物馆。庙底沟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类型,也是仰韶文化最为辉煌的阶段。庙底沟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十分适合人类耕种定居,因此植被繁茂、动物壮美。此地出土的动植物标本中,常见的农作物有粟、黍、水稻、大豆等,植物有草木樨、胡枝子、藜、马唐、狗尾草、野茉莉等,果类植物则有李属、葡萄属、橡子、枣等。常见的动物有鸡、猪、狗、黄牛、梅花鹿、马鹿以及部分鸟类,空前丰富的物质生活孕育了庙底沟文化丹青不渝的彩陶艺术。
博物馆中满墙满架的彩陶器将自己极强的装饰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制作者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将各色矿物颜料绘饰在夹砂红陶烧制的器物上,线条似行云流水,笔锋如游丝袅空,一器一绘,绝无雷同。5500年前的某个夏日,处于庙底沟文化圈内的华山脚下,能工巧匠们在黄色的陶器上用妙
从裴李岗向西230公里左右是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此地的记忆或许跟我一样停留在各类文献对“渑池会”的精彩描写中,而不知耳熟能详仰韶文化竟自此发源。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坐落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原之上,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向北可达韶山,仰韶村之名即取“仰望韶山”之意。园中芳草如积、繁花似锦,园外两条早已干涸的巨大环壕分属仰韶时期和稍晚的龙山时期,表明此地在距今7000-4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先民生息繁衍之所。公园内以韶源、韶乐、韶华三个广场为中心坐落着各种遗址标识,这一设计建造方案或许是为了反映仰韶文化以中心广场为核心、半地穴式房屋成组环绕的聚落布局。考古发现,仰韶村遗址中的房屋有大有小,大型房屋为母系家族公共活动场所,小型房屋为对偶婚夫妻临时住所。这表明仰韶人已经形成了以母系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群体,相比于裴李岗人,其社会复杂性正在进一步发展。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进步的需要。
仰韶村紧邻黄河,具有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河水冲积而呈的广袤平原也为大面积种植粟、黍提供了最佳环境。大田耕作和谷物增加又让先民摸索出了驯养动物的方法,而出于食用各种肉类的需求,仰韶人不得不改进生产生活工具,石锛、玉斧、陶甑、陶甗、陶盆等器具的形制逐渐完善,不仅越发便于使用,更慢慢地有了审美意义。
紧邻遗址公园的仰韶文化博物馆里,除了仰韶文化常见的各类陶器和遗迹外,还陈列着一件特殊的陶缸残片,它与众多文物“同居”在巨大的展柜中,初看并不起眼,但定睛细瞧便能发现烙印其上的一枚清晰指纹,据考古学家验证应当是来自一位20-30岁男性的右手拇指。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它的出现都开启了仰韶先民对美的认知。自此,指纹成为仰韶彩陶器上的主要装饰元素,在黑、红、黄三色绘就的天地万物间或隐或现的存在着,指尖轻点,描塑出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博物馆时,我忽觉此地高树斜草的斑斑光影间萦绕着一种奇妙的历史宿命感:7000年前,仰韶文化的诞生为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撕开蒙翳,带来第一缕曙光;而100多年前,又正是它的发现使风雨飘摇的中华文明重现光彩,寻回失落的尊严。
仰韶村遗址虽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圣地,但要全面领略仰韶文化的精妙,还得走进位于三门峡市的庙底沟博物馆。庙底沟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类型,也是仰韶文化最为辉煌的阶段。庙底沟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十分适合人类耕种定居,因此植被繁茂、动物壮美。此地出土的动植物标本中,常见的农作物有粟、黍、水稻、大豆等,植物有草木樨、胡枝子、藜、马唐、狗尾草、野茉莉等,果类植物则有李属、葡萄属、橡子、枣等。常见的动物有鸡、猪、狗、黄牛、梅花鹿、马鹿以及部分鸟类,空前丰富的物质生活孕育了庙底沟文化丹青不渝的彩陶艺术。
博物馆中满墙满架的彩陶器将自己极强的装饰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制作者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将各色矿物颜料绘饰在夹砂红陶烧制的器物上,线条似行云流水,笔锋如游丝袅空,一器一绘,绝无雷同。5500年前的某个夏日,处于庙底沟文化圈内的华山脚下,能工巧匠们在黄色的陶器上用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