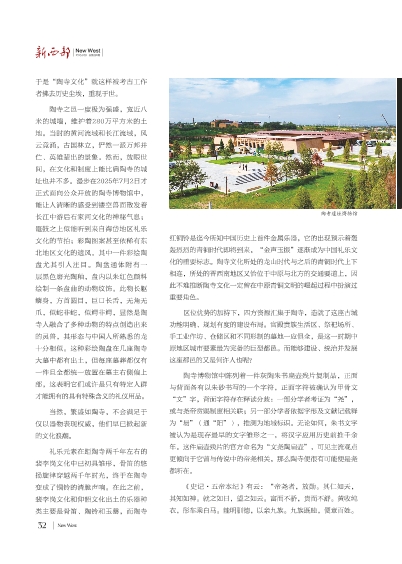黄河岸边的华夏序章

陶寺遗址博物馆
于是“陶寺文化”就这样被考古工作者拂去历史尘埃,重现于世。
陶寺之邑一度极为强盛,宽近八米的城墙,维护着280万平方米的土地。当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风云竞涌,古国林立,俨然一派万邦并伫、英雄辈出的景象。然而,放眼世间,在文化和制度上能比肩陶寺的城址也并不多。漫步在2025年7月2日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的陶寺博物馆中,能让人清晰的感受到镂空兽面散发着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秘气息;鼍鼓之上似能听到来自海岱地区礼乐文化的节拍;彩陶图案甚至依稀有东北地区文化的遗风。其中一件彩绘陶盘尤其引人注目。陶盘通体附有一层黑色磨光陶釉,盘内以朱红色颜料绘制一条盘曲的动物纹饰。此物长躯鳞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鳄非鳄,显然是陶寺人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灵兽,其形态与中国人所熟悉的龙十分相似。这种彩绘陶盘在几座陶寺大墓中都有出土,但每座墓葬都仅有一件且全都统一放置在墓主右侧偏上部,这表明它们或许是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拥有的具有特殊含义的礼仪用品。
当然,繁盛如陶寺,不会满足于仅以器物表现权威,他们早已掀起新的文化浪潮。
礼乐元素在距陶寺两千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中已初具雏形,骨笛的悠扬旋律穿越两千年时光,终于在陶寺变成了铜铃的清脆声响。在此之前,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出土的乐器种类主要是骨笛、陶铃和玉罄,而陶寺红铜铃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首件金属乐器,它的出现预示着轰轰烈烈的青铜时代即将到来,“金声玉振”逐渐成为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标志。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与之后的青铜时代上下相连,所处的晋西南地区又恰位于中原与北方的交通要道上,因此不难推断陶寺文化一定曾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区位优势的加持下,四方资源汇集于陶寺,造就了这座古城功能明确、规划有度的建设布局。官殿贵族生活区、祭祀场所、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不同形制的墓地一应俱全,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城市要素最为完备的巨型都邑。而能够建设、统治并发展这座都邑的又是何许人也呢?
陶寺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件灰陶朱书扁壶残片复制品,正面与背面各有以朱砂书写的一个字符,正面字符被确认为甲骨文“ 文”字,背面字符存在释读分歧:一部分学者考证为“尧” ,或与尧帝赏赐制度相关联;另一部分学者依据字形及文献记载释为“昜”(通“阳”),推测为地域标识。无论如何,朱书文字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将汉字应用历史前推千余年。这件扁壶残片的官方命名为“文尧陶扁壶”,可见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它曾与传说中的帝尧相关,那么陶寺便很有可能便是尧都所在。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