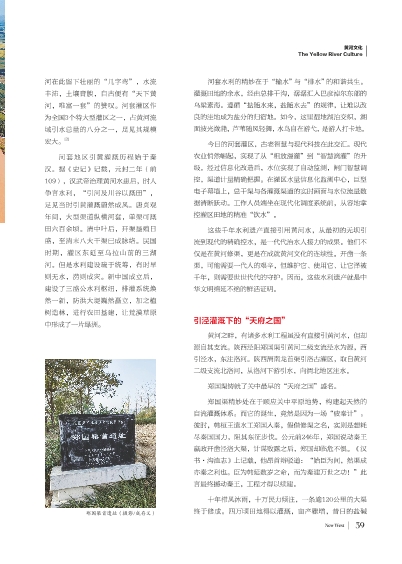黄河水利 生生不息

郑国渠首遗址(摄影/成存义)
河在此留下壮丽的“几字弯”,水流丰沛,土壤膏腴,自古便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赞叹。河套灌区作为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占黄河流域引水总量的八分之一,足见其规模宏大。 [2]
河套地区引黄灌溉历程始于秦汉。据《史记》记载,元封二年(前109) ,汉武帝治理黄河水患后,时人争言水利,“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足见当时引黄灌溉蔚然成风。唐贞观年间,大型渠道纵横河套,单渠可溉田六百余顷。清中叶后,开渠垦殖日盛,至清末八大干渠已成脉络。民国时期,灌区东延至乌拉山前的三湖河。但是水利建设疏于统筹,有时旱则无水,涝则成灾。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了三盛公水利枢纽,排灌系统焕然一新,防洪大堤巍然矗立,加之植树造林,进行农田基建,让荒漠草原中形成了一片绿洲。
河套水利的精妙在于“输水”与“排水”的和谐共生。灌溉田地的余水,经由总排干沟,潺潺汇入巴彦淖尔东部的乌梁素海。遵循“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规律,让难以改良的洼地成为盐分的归宿地。如今,这里湿地湖泊交织,湖面波光潋滟,芦苇随风轻舞,水鸟自在游弋,是游人打卡地。
今日的河套灌区,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在此交汇。现代农业悄然崛起,实现了从“粗放漫灌”到“智慧滴灌”的升级。经过信息化改造后,水位实现了自动监测,闸门智慧调控,渠道计量精确把握。在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巨型电子幕墙上,总干渠与各灌溉渠道的实时画面与水位流量数据清晰跃动。工作人员端坐在现代化调度系统前,从容地掌控灌区田地的精准“饮水” 。
这些千年水利遗产直接引用黄河水,从最初的无坝引流到现代的精确控水,是一代代治水人接力的成果。他们不仅是在黄河修渠,更是在成就黄河文化的连续性。开凿一条渠,可能需要一代人的艰辛,但维护它、使用它、让它泽被千年,则需要世世代代的守护。因而,这些水利遗产就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鲜活证明。
引泾灌溉下的“天府之国”
黄河之畔,有诸多水利工程虽没有直接引黄河水,但却源自其支流。陕西泾阳郑国渠引黄河二级支流泾水为源,西引泾水,东注洛河。陕西渭南龙首渠引洛古灌区,取自黄河二级支流北洛河,从洛河下游引水,向渭北地区注水。
郑国渠铸就了关中最早的“天府之国”盛名。
郑国渠精妙处在于顺应关中平原地势,构建起天然的自流灌溉体系。而它的诞生,竟然是因为一场“疲秦计” 。彼时,韩桓王遣水工郑国入秦,假借修渠之名,实则是想耗尽秦国国力,阻其东征步伐。公元前246年,郑国说动秦王嬴政开凿泾洛大渠,计谋败露之后,郑国却临危不惧。《汉书·沟洫志》上记载,他昂首辩驳道:“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此言最终撼动秦王,工程才得以续建。
十年栉风沐雨,十万民力倾注,一条逾120公里的大渠终于修成。四万顷田地得以灌溉,亩产骤增,昔日的盐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