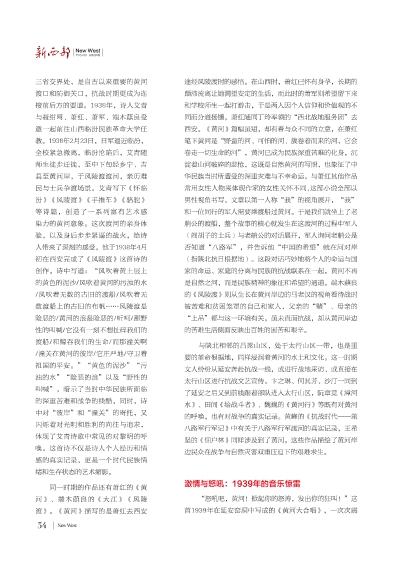民族的脉搏— —黄河文学探析
三省交界处,是自古以来重要的黄河渡口和防御关口,抗战时期更成为连接前后方的要道。1938年,诗人艾青与聂绀弩、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受邀一起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38年2月23日,日军逼近临汾,全校紧急撤离,临汾沦陷后,艾青随师生徒步迁徙,至中下旬经乡宁、吉县至黄河岸,于风陵渡渡河,亲历难民与士兵争渡场景。艾青写下《怀临汾》《风陵渡》《手推车》《骆驼》等诗篇,创造了一系列富有艺术感染力的黄河意象。这次渡河的亲身体验,以及身后步步紧逼的战火,给诗人带来了深刻的感受,他于1938年4月初在西安完成了《风陵渡》这首诗的创作。诗中写道:“风吹着黄土层上的黄色的泥沙/风吹着黄河的污浊的水/风吹着无数的古旧的渡船/风吹着无数渡船上的古旧的布帆……风陵渡是险恶的/黄河的浪是险恶的/听呵/那野性的叫喊/它没有一刻不想扯碎我们的渡船/和鲸吞我们的生命/而那潼关啊/潼关在黄河的彼岸/它庄严地/守卫着祖国的平安。”“黄色的泥沙”“污浊的水”“险恶的浪”以及“野性的叫喊”,暗示了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苦难和战争的残酷,同时,诗中对“彼岸”和“潼关”的寄托,又闪烁着对光明和胜利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艾青诗歌中常见的对黎明的呼唤。这首诗不仅是诗人个人经历和情感的真实记录,更是一个时代民族情绪和生存状态的艺术缩影。
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萧红的《黄河》、端木蕻良的《大江》《风陵渡》。《黄河》描写的是萧红去西安途经风陵渡时的感悟。在山西时,萧红已怀有身孕,长期的颠沛流离让她渴望安定的生活,而此时的萧军则希望留下来和学校师生一起打游击,于是两人因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萧红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黄河》篇幅虽短,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立意,在萧红笔下黄河是“野蛮的河、可怕的河、簇卷着而来的河,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黄河已成为民族深重苦难的化身,沉淀着山河破碎的悲怆,这既是自然黄河的写照,也象征了中华民族当时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与不幸命运。与萧红其他作品常用女性人物来体现作家的女性关怀不同,这部小说全部以男性视角书写,文章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我”和一位同行的军人需要乘渡船过黄河。于是我们就坐上了老艄公的渡船,整个故事的核心就发生在这渡河的过程中军人(阎胡子的士兵)与老艄公的对话展开,军人询问老艄公是否知道“八路军”,并告诉他“中国的希望”就在河对岸(指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段对话巧妙地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家庭的分离与民族的抗战联系在一起,黄河不再是自然之河,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希望的通道。端木蕻良的《风陵渡》则从生长在黄河岸边的马老汉的视角看待战时被苦难和贫困笼罩的自己和家人,父亲的“赌”、母亲的“上吊”都与这一环境有关,虽未直面抗战,却从黄河岸边的苦难生活侧面反映出百姓的困苦和艰辛。
与陕北相邻的吕梁山区,处于太行山区一带,也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同样浸润着黄河的水土和文化。这一时期文人纷纷从延安奔赴抗战一线,或进行战地采访、或直接在太行山区进行抗战文艺宣传,卞之琳、何其芳、沙汀一同到了延安之后又到前线跟着部队进入太行山区,阮章竞《漳河水》、田间《给战斗者》、魏巍的《黄河行》等既有对黄河的呼唤,也有对战争的真实记录。黄峰的《抗战时代——第八路军行军记》中有关于八路军行军渡河的真实记录,王希坚的《佃户林》同样涉及到了黄河,这些作品描绘了黄河岸边民众在战争与自然灾害双重压迫下的艰难求生。
激情与怒吼:1939年的音乐惊雷
“怒吼吧,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这首1939年在延安窑洞中写成的《黄河大合唱》,一次次震
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萧红的《黄河》、端木蕻良的《大江》《风陵渡》。《黄河》描写的是萧红去西安途经风陵渡时的感悟。在山西时,萧红已怀有身孕,长期的颠沛流离让她渴望安定的生活,而此时的萧军则希望留下来和学校师生一起打游击,于是两人因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萧红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黄河》篇幅虽短,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立意,在萧红笔下黄河是“野蛮的河、可怕的河、簇卷着而来的河,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黄河已成为民族深重苦难的化身,沉淀着山河破碎的悲怆,这既是自然黄河的写照,也象征了中华民族当时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与不幸命运。与萧红其他作品常用女性人物来体现作家的女性关怀不同,这部小说全部以男性视角书写,文章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我”和一位同行的军人需要乘渡船过黄河。于是我们就坐上了老艄公的渡船,整个故事的核心就发生在这渡河的过程中军人(阎胡子的士兵)与老艄公的对话展开,军人询问老艄公是否知道“八路军”,并告诉他“中国的希望”就在河对岸(指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段对话巧妙地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家庭的分离与民族的抗战联系在一起,黄河不再是自然之河,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希望的通道。端木蕻良的《风陵渡》则从生长在黄河岸边的马老汉的视角看待战时被苦难和贫困笼罩的自己和家人,父亲的“赌”、母亲的“上吊”都与这一环境有关,虽未直面抗战,却从黄河岸边的苦难生活侧面反映出百姓的困苦和艰辛。
与陕北相邻的吕梁山区,处于太行山区一带,也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同样浸润着黄河的水土和文化。这一时期文人纷纷从延安奔赴抗战一线,或进行战地采访、或直接在太行山区进行抗战文艺宣传,卞之琳、何其芳、沙汀一同到了延安之后又到前线跟着部队进入太行山区,阮章竞《漳河水》、田间《给战斗者》、魏巍的《黄河行》等既有对黄河的呼唤,也有对战争的真实记录。黄峰的《抗战时代——第八路军行军记》中有关于八路军行军渡河的真实记录,王希坚的《佃户林》同样涉及到了黄河,这些作品描绘了黄河岸边民众在战争与自然灾害双重压迫下的艰难求生。
激情与怒吼:1939年的音乐惊雷
“怒吼吧,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这首1939年在延安窑洞中写成的《黄河大合唱》,一次次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