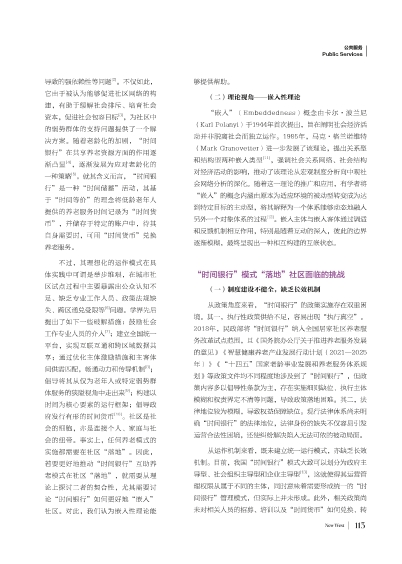“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落地”社区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导致的强依赖性等问题 。 [2]不仅如此,它由于被认为能够促进社区网络的构建,有助于缓解社会排斥、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包容目标 ,为社区中[3]的弱势群体的支持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时间银行”在共享养老资源方面的作用逐 [4]渐凸显 ,逐渐发展为应对老龄化的 [5 ]一种策略 。就其含义而言,“时间银行”是一种“时间储蓄”活动,其基于“时间等价”的理念将低龄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时间记录为“时间货币”,并储存于特定的账户中,待其自身需要时,可用“时间货币”兑换养老服务。
不过,其理想化的运作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可谓是举步维艰,在城市社区试点过程中主要暴露出公众认知不足、缺乏专业工作人员、政策法规缺失、跨区通兑受限等[6 ]问题。学界先后提出了如下一些破解措施: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介入 ; 建立全国统一[7 ]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跨区域数据共享;通过优化主体激励措施和主客体
[8]间供需匹配,畅通动力和传导机制 ;倡导将其从仅为老年人或特定弱势群[9]体服务的狭隘视角中走出来 ;构建以时间为核心要素的运行框架;倡导政 [ 10]府发行有形的时间货币 。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亦是连接个人、家庭与社会的纽带。事实上,任何养老模式的实施都需要在社区“落地”。因此,若要更好地推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社区“落地”,就需要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契合性,尤其需要讨论“时间银行”如何更好地“嵌入”社区。对此,我们认为嵌入性理论能够提供帮助。
(二)理论视角——嵌入性理论
“嵌入”(Embeddedness)概念由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于1944年首次提出,旨在阐明社会经济活动并非脱离社会而独立运作。1985年,马克·格兰诺维特( M ark Granovetter)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关系型和结构型两种嵌入类型 , 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结构[11]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推动了该理论从宏观制度分析向中观社会网络分析的深化。随着这一理论的推广和应用,有学者将“嵌入”的概念内涵由原本为适应环境的被动型转变成为达到特定目标的主动型,将其解释为一个体系能够动态地融入[12]另外一个对象体系的过程 。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通过调适和反馈机制相互作用,特别是随着互动的深入,彼此的边界逐渐模糊,最终呈现出一种相互构建的互嵌状态。
“时间银行”模式“落地”社区面临的挑战
(一)制度建设不健全,缺乏长效机制
从政策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政策实施存在双重困境。其一,执行性政策供给不足,容易出现“执行真空” 。2018年,民政部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 2025年)》《“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政策文件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时间银行”,但政策内容多以倡导性条款为主,存在实施细则缺位、执行主体模糊和权责界定不清等问题,导致政策落地困难。其二,法律地位较为模糊,导致权益保障缺位。现行法律体系尚未明确“时间银行”的法律地位,法律身份的缺失不仅容易引发运营合法性困境,还使纠纷解决陷入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
从运作机制来看,既未建立统一运行模式,亦缺乏长效机制。目前,我国“时间银行”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 ,这就使得其运营管理权限从属于不同的主体,同时意味着需要形成统一的“时间银行”管理模式,但实际上并未形成。此外,相关政策尚未对相关人员的招募、培训以及“时间货币”如何兑换、转[13]
不过,其理想化的运作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可谓是举步维艰,在城市社区试点过程中主要暴露出公众认知不足、缺乏专业工作人员、政策法规缺失、跨区通兑受限等[6 ]问题。学界先后提出了如下一些破解措施: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介入 ; 建立全国统一[7 ]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跨区域数据共享;通过优化主体激励措施和主客体
[8]间供需匹配,畅通动力和传导机制 ;倡导将其从仅为老年人或特定弱势群[9]体服务的狭隘视角中走出来 ;构建以时间为核心要素的运行框架;倡导政 [ 10]府发行有形的时间货币 。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亦是连接个人、家庭与社会的纽带。事实上,任何养老模式的实施都需要在社区“落地”。因此,若要更好地推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社区“落地”,就需要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契合性,尤其需要讨论“时间银行”如何更好地“嵌入”社区。对此,我们认为嵌入性理论能够提供帮助。
(二)理论视角——嵌入性理论
“嵌入”(Embeddedness)概念由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于1944年首次提出,旨在阐明社会经济活动并非脱离社会而独立运作。1985年,马克·格兰诺维特( M ark Granovetter)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关系型和结构型两种嵌入类型 , 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结构[11]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推动了该理论从宏观制度分析向中观社会网络分析的深化。随着这一理论的推广和应用,有学者将“嵌入”的概念内涵由原本为适应环境的被动型转变成为达到特定目标的主动型,将其解释为一个体系能够动态地融入[12]另外一个对象体系的过程 。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通过调适和反馈机制相互作用,特别是随着互动的深入,彼此的边界逐渐模糊,最终呈现出一种相互构建的互嵌状态。
“时间银行”模式“落地”社区面临的挑战
(一)制度建设不健全,缺乏长效机制
从政策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政策实施存在双重困境。其一,执行性政策供给不足,容易出现“执行真空” 。2018年,民政部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 2025年)》《“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政策文件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时间银行”,但政策内容多以倡导性条款为主,存在实施细则缺位、执行主体模糊和权责界定不清等问题,导致政策落地困难。其二,法律地位较为模糊,导致权益保障缺位。现行法律体系尚未明确“时间银行”的法律地位,法律身份的缺失不仅容易引发运营合法性困境,还使纠纷解决陷入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
从运作机制来看,既未建立统一运行模式,亦缺乏长效机制。目前,我国“时间银行”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 ,这就使得其运营管理权限从属于不同的主体,同时意味着需要形成统一的“时间银行”管理模式,但实际上并未形成。此外,相关政策尚未对相关人员的招募、培训以及“时间货币”如何兑换、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