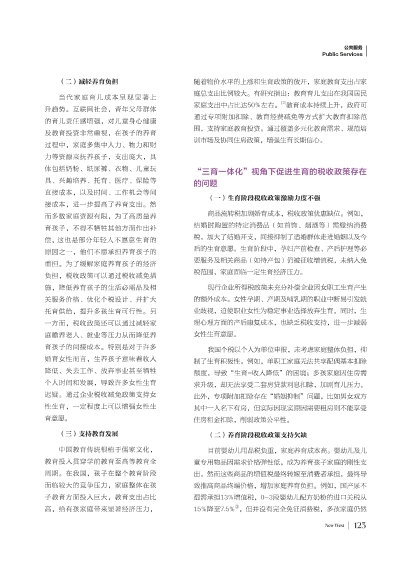“三育一体化”视角下 促进生育的税收政策优化研究
(二)减轻养育负担
当代家庭育儿成本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互联网社会,青年父母群体的育儿责任感增强,对儿童身心健康及教育投资非常重视,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家庭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来抚养孩子,支出庞大,具体包括奶粉、纸尿裤、衣物、儿童玩具、兴趣培养、托育、医疗、保险等直接成本,以及时间、工作机会等间接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养育支出。然而多数家庭资源有限,为了高质量养育孩子,不得不牺牲其他方面作出补偿,这也是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愿承担养育孩子的重担。为了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税收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措施,降低养育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及相关服务价格、优化个税设计、并扩大托育供给,提升多孩生育可行性。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减轻家庭赡养老人、就业等压力从而降低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特别是对于许多婚育女性而言,生养孩子意味着收入降低、失去工作、放弃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时间和发展,导致许多女性生育迟疑。通过企业税收减免政策支持女性生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女性生育意愿。
(三)支持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传统根植于儒家文化,教育投入贯穿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周期。在我国,孩子在整个教育阶段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家庭整体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巨大,教育支出占比高,给有孩家庭带来显著经济压力,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和生育政策的放开,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较大。有研究指出:教育育儿支出在我国居民家庭支出中占比达50%左右。[2] 教育成本持续上升,政府可通过专项附加扣除、教育经费减免等方式扩大教育扣除范围,支持家庭教育投资。通过覆盖多元化教育需求、规范培训市场及协同住房政策,增强生育长期信心。
“三育一体化”视角下促进生育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生育阶段税收政策激励力度不强
商品流转税加剧婚育成本,税收政策优惠缺位。例如,结婚时购置的特定消费品(如首饰、烟酒等)需缴纳消费税,加大了结婚开支,间接抑制了适婚群体走进婚姻以及今后的生育意愿。生育阶段中,孕妇产前检查、产后护理等必要服务及相关商品(如待产包)仍被征收增值税,未纳入免税范围,家庭面临一定生育经济压力。
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未充分补偿企业因女职工生育产生的额外成本。女性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职业中断易引发就业歧视,迫使职业女性为稳定事业选择放弃生育。同时,生理心理方面的产后康复成本,也缺乏税收支持,进一步减弱女性生育意愿。
我国个税以个人为单位申报,未考虑家庭整体负担,抑制了生育积极性。例如,单职工家庭无法共享配偶基本扣除额度,导致“生育=收入降低”的困境;多孩家庭因住房需求升级,却无法享受二套房贷款利息扣除,加剧育儿压力。此外,专项附加扣除存在“婚姻抑制”问题,比如男女双方其中一人名下有房,但实际因现实原因需要租房则不能享受住房租金扣除,削弱政策公平性。
(二)养育阶段税收政策支持欠缺
目前婴幼儿用品税负重,家庭养育成本高。婴幼儿及儿童专用物品因需求价格弹性低,成为养育孩子家庭的刚性支出,然而这些商品的增值税最终转嫁至消费者承担,最终导致推高商品终端价格,增加家庭养育负担。例如,国产尿不湿需承担13%增值税,0-3段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进口关税从15%降至7.5%③ , 但并没有完全免征消费税,多孩家庭仍然
当代家庭育儿成本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互联网社会,青年父母群体的育儿责任感增强,对儿童身心健康及教育投资非常重视,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家庭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来抚养孩子,支出庞大,具体包括奶粉、纸尿裤、衣物、儿童玩具、兴趣培养、托育、医疗、保险等直接成本,以及时间、工作机会等间接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养育支出。然而多数家庭资源有限,为了高质量养育孩子,不得不牺牲其他方面作出补偿,这也是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愿承担养育孩子的重担。为了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税收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措施,降低养育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及相关服务价格、优化个税设计、并扩大托育供给,提升多孩生育可行性。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减轻家庭赡养老人、就业等压力从而降低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特别是对于许多婚育女性而言,生养孩子意味着收入降低、失去工作、放弃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时间和发展,导致许多女性生育迟疑。通过企业税收减免政策支持女性生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女性生育意愿。
(三)支持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传统根植于儒家文化,教育投入贯穿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周期。在我国,孩子在整个教育阶段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家庭整体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巨大,教育支出占比高,给有孩家庭带来显著经济压力,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和生育政策的放开,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较大。有研究指出:教育育儿支出在我国居民家庭支出中占比达50%左右。[2] 教育成本持续上升,政府可通过专项附加扣除、教育经费减免等方式扩大教育扣除范围,支持家庭教育投资。通过覆盖多元化教育需求、规范培训市场及协同住房政策,增强生育长期信心。
“三育一体化”视角下促进生育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生育阶段税收政策激励力度不强
商品流转税加剧婚育成本,税收政策优惠缺位。例如,结婚时购置的特定消费品(如首饰、烟酒等)需缴纳消费税,加大了结婚开支,间接抑制了适婚群体走进婚姻以及今后的生育意愿。生育阶段中,孕妇产前检查、产后护理等必要服务及相关商品(如待产包)仍被征收增值税,未纳入免税范围,家庭面临一定生育经济压力。
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未充分补偿企业因女职工生育产生的额外成本。女性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职业中断易引发就业歧视,迫使职业女性为稳定事业选择放弃生育。同时,生理心理方面的产后康复成本,也缺乏税收支持,进一步减弱女性生育意愿。
我国个税以个人为单位申报,未考虑家庭整体负担,抑制了生育积极性。例如,单职工家庭无法共享配偶基本扣除额度,导致“生育=收入降低”的困境;多孩家庭因住房需求升级,却无法享受二套房贷款利息扣除,加剧育儿压力。此外,专项附加扣除存在“婚姻抑制”问题,比如男女双方其中一人名下有房,但实际因现实原因需要租房则不能享受住房租金扣除,削弱政策公平性。
(二)养育阶段税收政策支持欠缺
目前婴幼儿用品税负重,家庭养育成本高。婴幼儿及儿童专用物品因需求价格弹性低,成为养育孩子家庭的刚性支出,然而这些商品的增值税最终转嫁至消费者承担,最终导致推高商品终端价格,增加家庭养育负担。例如,国产尿不湿需承担13%增值税,0-3段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进口关税从15%降至7.5%③ , 但并没有完全免征消费税,多孩家庭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