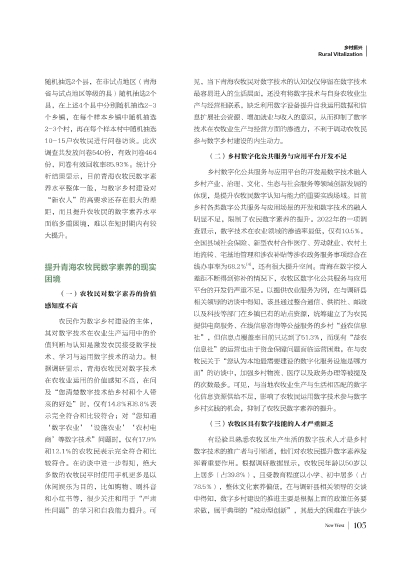数字乡村视域下 提升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的路径研究
随机抽选2个县,在非试点地区(青海省与试点地区等级的县)随机抽选2个县,在上述4个县中分别随机抽选2-3个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选2-3个村,再在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选10-15户农牧民进行问卷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40份,有效问卷46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85.93%。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目前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水平整体一般,与数字乡村建设对“新农人”的高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提升农牧民的数字素养水平面临多重困境,难以在短时期内有较大提升。
提升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困境
(一)农牧民对数字素养的价值感知度不高
农民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其对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运用中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是激发农民接受数字技术、学习与运用数字技术的动力。根据调研显示,青海农牧民对数字技术在农牧业运用的价值感知不高,在问及“您清楚数字技术给乡村和个人带来的好处”时,仅有14.8%和8.8%表示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对“您知道‘数字农业’‘设施农业’‘农村电商’等数字技术”问题时,仅有17.9%和12.1%的农牧民表示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在访谈中进一步得知,绝大多数的农牧民平时使用手机更多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比如购物、刷抖音和小红书等,很少关注和用于“严肃性问题”的学习和自我能力提升。可见,当下青海农牧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数字技术最容易进入的生活层面,还没有将数字技术与自身农牧业生产与经营相联系,缺乏利用数字设备提升自我运用数据和信息扩展社会资源、增加就业与收入的意识,从而抑制了数字技术在农牧业生产与经营方面的渗透力,不利于调动农牧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二)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应用平台开发不足
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应用平台的开发是数字技术融入乡村产业、治理、文化、生态与社会服务等领域创新发展的体现,是提升农牧民数字认知与能力的重要实践场域。目前乡村各类数字公共服务与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数字技术的融入明显不足,限制了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渗透率最低,仅有10.5% 。全国县域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劳动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管理和涉农补贴等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为68.2% ,[4]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青海在数字接入 差距不断得到弥补的情况下,农牧区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应用平台的开发仍严重不足。以提供农业服务为例,在与调研县相关领导的访谈中得知,该县通过整合通信、供销社、邮政以及科技等部门在乡镇已有的站点资源,统筹建立了为农民提供电商服务、在线信息咨询等公益服务的乡村“益农信息社”,但信息点覆盖率目前只达到了51.3%,而现有“益农信息社”的运营也由于资金保障问题面临运营困难。在与农牧民关于“您认为本地最需要建设的数字化服务设施是哪方面”的访谈中,加强乡村物流、医疗以及政务办理等被提及的次数最多。可见,与当地农牧业生产与生活相匹配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供给不足,影响了农牧民运用数字技术参与数字乡村实践的机会,抑制了农牧民数字素养的提升。
(三)农牧区具有数字技能的人才严重匮乏
有经验且熟悉农牧区生产生活的数字技术人才是乡村数字技术的推广者与引领者,他们对农牧民提升数字素养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农牧民年龄以50岁以上居多(占39.8%),且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居多(占78.5% ) ,整体文化素养偏低。在与调研县相关领导的交谈中得知,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主要是根据上面的政策任务要求做,属于典型的“被动型创新”,其最大的困难在于缺少
提升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困境
(一)农牧民对数字素养的价值感知度不高
农民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其对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运用中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是激发农民接受数字技术、学习与运用数字技术的动力。根据调研显示,青海农牧民对数字技术在农牧业运用的价值感知不高,在问及“您清楚数字技术给乡村和个人带来的好处”时,仅有14.8%和8.8%表示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对“您知道‘数字农业’‘设施农业’‘农村电商’等数字技术”问题时,仅有17.9%和12.1%的农牧民表示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在访谈中进一步得知,绝大多数的农牧民平时使用手机更多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比如购物、刷抖音和小红书等,很少关注和用于“严肃性问题”的学习和自我能力提升。可见,当下青海农牧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数字技术最容易进入的生活层面,还没有将数字技术与自身农牧业生产与经营相联系,缺乏利用数字设备提升自我运用数据和信息扩展社会资源、增加就业与收入的意识,从而抑制了数字技术在农牧业生产与经营方面的渗透力,不利于调动农牧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二)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应用平台开发不足
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应用平台的开发是数字技术融入乡村产业、治理、文化、生态与社会服务等领域创新发展的体现,是提升农牧民数字认知与能力的重要实践场域。目前乡村各类数字公共服务与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数字技术的融入明显不足,限制了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渗透率最低,仅有10.5% 。全国县域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劳动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管理和涉农补贴等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为68.2% ,[4]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青海在数字接入 差距不断得到弥补的情况下,农牧区数字化公共服务与应用平台的开发仍严重不足。以提供农业服务为例,在与调研县相关领导的访谈中得知,该县通过整合通信、供销社、邮政以及科技等部门在乡镇已有的站点资源,统筹建立了为农民提供电商服务、在线信息咨询等公益服务的乡村“益农信息社”,但信息点覆盖率目前只达到了51.3%,而现有“益农信息社”的运营也由于资金保障问题面临运营困难。在与农牧民关于“您认为本地最需要建设的数字化服务设施是哪方面”的访谈中,加强乡村物流、医疗以及政务办理等被提及的次数最多。可见,与当地农牧业生产与生活相匹配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供给不足,影响了农牧民运用数字技术参与数字乡村实践的机会,抑制了农牧民数字素养的提升。
(三)农牧区具有数字技能的人才严重匮乏
有经验且熟悉农牧区生产生活的数字技术人才是乡村数字技术的推广者与引领者,他们对农牧民提升数字素养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农牧民年龄以50岁以上居多(占39.8%),且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居多(占78.5% ) ,整体文化素养偏低。在与调研县相关领导的交谈中得知,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主要是根据上面的政策任务要求做,属于典型的“被动型创新”,其最大的困难在于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