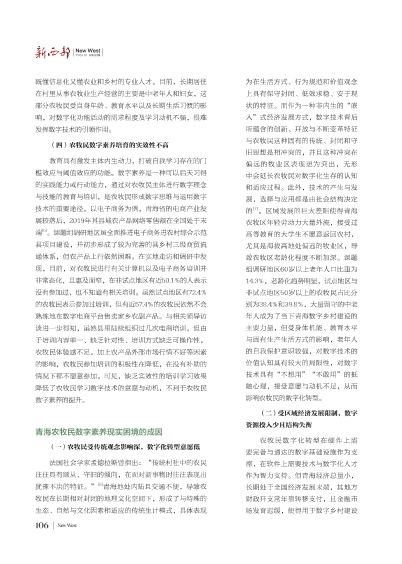数字乡村视域下 提升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的路径研究
既懂信息化又懂农业和乡村的专业人才。目前,长期居住在村里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和妇女,这部分农牧民受自身年龄、教育水平以及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对数字化功能活动的需求程度及学习动机不强,很难发挥数字技术的引领作用。
(四)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实效性不高
教育具有激发主体内生动力,打破自我学习存在的门槛效应与阈值效应的功能。数字素养是一种可以后天习得的实践能力或行动能力,通过对农牧民主体进行数字理念与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是农牧民形成数字思维与运用数字技术的重要途径。以电子商务为例,青海省的电商产业发展较落后,2019年其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在全国处于末端 。 [ 5]课题组调研地区虽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建设,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商贸流通体系,但农产品上行依然困难。在实地走访和调研中发现,目前,对农牧民进行有关计算机以及电子商务培训并非常态化,且惠及面窄,在非试点地区有近50.1%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也不知道有相关培训。虽然试点地区有72.4%的农牧民表示参加过培训,但有近57.4%的农牧民依然不会熟练地在数字电商平台售卖家乡农副产品。与相关领导访谈进一步得知,虽然县里陆续组织过几次电商培训,但由于培训内容单一、缺乏针对性、培训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农牧民体验感不足。加上农产品外部市场行情不好等因素的影响,农牧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在降低,在没有补助的情况下都不愿意参加。可见,缺乏实效性的培训学习效果降低了农牧民学习数字技术的意愿与动机,不利于农牧民数字素养的提升。
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现实困境的成因
(一)农牧民受传统观念影响深,数字化转型意愿低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指出:“传统村社中的农民往往具有顺从、守旧的倾向,在面对新事物时往往表现出[ 6]犹豫不决的特征。 ” 青海地处内陆且交通不便,导致农牧民在长期相对封闭的地理文化空间下,形成了与特殊的生态、自然与文化因素相适应的传统生计模式,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上具有保守封闭、低效求稳、安于现状的特征。而作为一种非内生的“嵌入”式经济发展方式,数字技术背后所蕴含的创新、开放与不断变革特征与农牧民这种固有的传统、封闭和守旧思想是相冲突的,并且这种冲突在偏远的牧业区表现更为突出,无形中会延长农牧民对数字化生存的认知和适应过程。此外,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选择与应用都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 。 [ 7 ] 区域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青海农牧区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愿意返回农村,尤其是海拔高地处偏远的牧业区,导致农牧区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课题组调研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4.3% ,老龄化趋势明显,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50岁以上的农牧民占比分别为38.4%和39.8%,大量留守的中老年人成为了当下青海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但受身体机能、教育水平与固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对数字技术具有“不想用”“不敢用”的抵触心理,接受意愿与动机不足,从而影响农牧民的数字化转型。
(二)受区域经济发展限制,数字资源投入少且结构失衡
农牧民数字化转型在硬件上需要完备与通达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在软件上需要技术与数字化人才作为智力支持。但青海经济总量小,长期处于全国经济发展末端,其地方财政开支常年靠转移支付,且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使得用于数字乡村建设
(四)农牧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实效性不高
教育具有激发主体内生动力,打破自我学习存在的门槛效应与阈值效应的功能。数字素养是一种可以后天习得的实践能力或行动能力,通过对农牧民主体进行数字理念与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是农牧民形成数字思维与运用数字技术的重要途径。以电子商务为例,青海省的电商产业发展较落后,2019年其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在全国处于末端 。 [ 5]课题组调研地区虽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建设,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商贸流通体系,但农产品上行依然困难。在实地走访和调研中发现,目前,对农牧民进行有关计算机以及电子商务培训并非常态化,且惠及面窄,在非试点地区有近50.1%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也不知道有相关培训。虽然试点地区有72.4%的农牧民表示参加过培训,但有近57.4%的农牧民依然不会熟练地在数字电商平台售卖家乡农副产品。与相关领导访谈进一步得知,虽然县里陆续组织过几次电商培训,但由于培训内容单一、缺乏针对性、培训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农牧民体验感不足。加上农产品外部市场行情不好等因素的影响,农牧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在降低,在没有补助的情况下都不愿意参加。可见,缺乏实效性的培训学习效果降低了农牧民学习数字技术的意愿与动机,不利于农牧民数字素养的提升。
青海农牧民数字素养现实困境的成因
(一)农牧民受传统观念影响深,数字化转型意愿低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指出:“传统村社中的农民往往具有顺从、守旧的倾向,在面对新事物时往往表现出[ 6]犹豫不决的特征。 ” 青海地处内陆且交通不便,导致农牧民在长期相对封闭的地理文化空间下,形成了与特殊的生态、自然与文化因素相适应的传统生计模式,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上具有保守封闭、低效求稳、安于现状的特征。而作为一种非内生的“嵌入”式经济发展方式,数字技术背后所蕴含的创新、开放与不断变革特征与农牧民这种固有的传统、封闭和守旧思想是相冲突的,并且这种冲突在偏远的牧业区表现更为突出,无形中会延长农牧民对数字化生存的认知和适应过程。此外,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选择与应用都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 。 [ 7 ] 区域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青海农牧区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愿意返回农村,尤其是海拔高地处偏远的牧业区,导致农牧区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课题组调研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4.3% ,老龄化趋势明显,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50岁以上的农牧民占比分别为38.4%和39.8%,大量留守的中老年人成为了当下青海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但受身体机能、教育水平与固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对数字技术具有“不想用”“不敢用”的抵触心理,接受意愿与动机不足,从而影响农牧民的数字化转型。
(二)受区域经济发展限制,数字资源投入少且结构失衡
农牧民数字化转型在硬件上需要完备与通达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在软件上需要技术与数字化人才作为智力支持。但青海经济总量小,长期处于全国经济发展末端,其地方财政开支常年靠转移支付,且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使得用于数字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