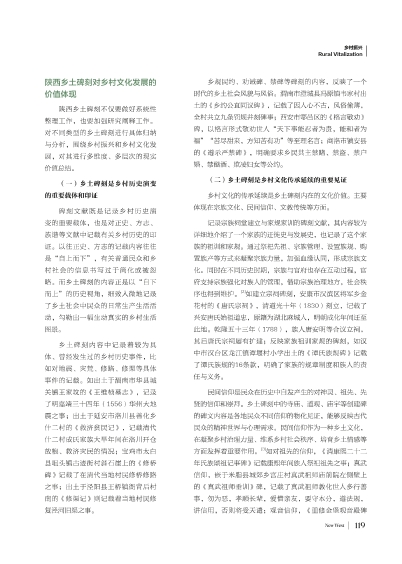深入挖掘陕西乡土碑刻价值 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陕西乡土碑刻对乡村文化发展的 价值体现
陕西乡土碑刻不仅要做好系统性整理工作,也要加强研究阐释工作。对不同类型的乡土碑刻进行具体归纳与分析,围绕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对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现实价值总结。
(一)乡土碑刻是乡村历史演变的重要载体和印证
碑刻文献既是记录乡村历史演变的重要载体,也是对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献中记载有关乡村历史的印证。以往正史、方志的记载内容往往是“自上而下”,有关普通民众和乡村社会的信息书写过于简化或被忽略。而乡土碑刻的内容正是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乡土社会中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勾勒出一幅生动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
乡土碑刻内容中记录着较为具体、曾经发生过的乡村历史事件,比如对地震、灾荒、修路、修渠等具体事件的记载。如出土于渭南市华县城关镇王家坟的《王维桢墓志》,记录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华州大地震之事;出土于延安市洛川县善化乡什二村的《救济贫民记》,记载清代什二村成氏家族大旱年间在洛川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情况;宝鸡市太白县咀头镇古迹街村斜石崖上的《修桥碑》记载了在清代当地村民修桥修路之事;出土于泾阳县王桥镇衙背后村南的《修渠记》则记载着当地村民修复泾河旧渠之事。
乡规民约、劝诫碑、禁碑等碑刻的内容,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乡土社会风貌与风俗。渭南市澄城县冯原镇韦家村出土的《乡约公直同议碑》,记载了因人心不古,风俗偷薄,全村共立九条罚规并刻碑事;西安市鄠邑区的《格言敬劝》碑,以格言形式敬劝世人“天下事能忍者为贵,能和者为福”“苦尽甜来,方知苦有功”等至理名言;商洛市镇安县的《遵示严禁碑》,明确要求乡民共主禁赌、禁盗、禁户婚、禁酗酒、欺凌妇女等公约。
(二)乡土碑刻是乡村文化传承延续的重要见证
乡村文化的传承延续是乡土碑刻内在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宗族文化、民间信仰、文教传统等方面。
记录宗族祠堂建立与家规家训的碑刻文献,其内容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个家族的迁徙史与发展史,也记录了这个家族的祖训和家规。通过祭祀先祖、宗族管理、设置族规、购置族产等方式来凝聚宗族力量,加强血缘认同,形成宗族文化。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宗族与官府也存在互动过程,官府支持宗族强化对族人的管理,借助宗族治理地方,社会秩序也得到维护。 [2] 如建立宗祠碑刻,安康市汉滨区将军乡金花村的《唐氏宗祠》,清道光十年(1830)刻立,记载了兴安唐氏始祖道忠,原籍为湖北麻城人,明朝成化年间迁至此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族人唐安明等合议立祠,其后唐氏宗祠屡有扩建;反映家族祖训家规的碑刻,如汉中市汉台区龙江镇谭堰村小学出土的《谭氏族规碑》记载了谭氏族规的16条款,明确了家族的规章制度和族人的责任与义务。
民间信仰是民众在历史中自发产生的对神灵、祖先、先贤的信仰和崇拜。乡土碑刻中的寺庙、道观、庙宇等创建碑的碑文内容是各地民众不同信仰的物化见证,能够反映古代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心理需求。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乡土文化,在凝聚乡村治理力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培育乡土情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 如对祖先的信仰,《清康熙二十二年氏族颂祖记事碑》记载康熙年间族人祭祀祖先之事;真武信仰,嵌于米脂县城郊乡宫庄村真武祖师庙前院左侧壁上的《真武祖师垂训》碑,记载了真武祖师教化世人多行善事,勿为恶,孝顺长辈,爱惜亲友,要守本分,遵法规,讲信用,否则将受天谴;观音信仰,《重修金堡观音殿碑
陕西乡土碑刻不仅要做好系统性整理工作,也要加强研究阐释工作。对不同类型的乡土碑刻进行具体归纳与分析,围绕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对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现实价值总结。
(一)乡土碑刻是乡村历史演变的重要载体和印证
碑刻文献既是记录乡村历史演变的重要载体,也是对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献中记载有关乡村历史的印证。以往正史、方志的记载内容往往是“自上而下”,有关普通民众和乡村社会的信息书写过于简化或被忽略。而乡土碑刻的内容正是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视角,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乡土社会中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勾勒出一幅生动真实的乡村生活图景。
乡土碑刻内容中记录着较为具体、曾经发生过的乡村历史事件,比如对地震、灾荒、修路、修渠等具体事件的记载。如出土于渭南市华县城关镇王家坟的《王维桢墓志》,记录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华州大地震之事;出土于延安市洛川县善化乡什二村的《救济贫民记》,记载清代什二村成氏家族大旱年间在洛川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情况;宝鸡市太白县咀头镇古迹街村斜石崖上的《修桥碑》记载了在清代当地村民修桥修路之事;出土于泾阳县王桥镇衙背后村南的《修渠记》则记载着当地村民修复泾河旧渠之事。
乡规民约、劝诫碑、禁碑等碑刻的内容,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乡土社会风貌与风俗。渭南市澄城县冯原镇韦家村出土的《乡约公直同议碑》,记载了因人心不古,风俗偷薄,全村共立九条罚规并刻碑事;西安市鄠邑区的《格言敬劝》碑,以格言形式敬劝世人“天下事能忍者为贵,能和者为福”“苦尽甜来,方知苦有功”等至理名言;商洛市镇安县的《遵示严禁碑》,明确要求乡民共主禁赌、禁盗、禁户婚、禁酗酒、欺凌妇女等公约。
(二)乡土碑刻是乡村文化传承延续的重要见证
乡村文化的传承延续是乡土碑刻内在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宗族文化、民间信仰、文教传统等方面。
记录宗族祠堂建立与家规家训的碑刻文献,其内容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个家族的迁徙史与发展史,也记录了这个家族的祖训和家规。通过祭祀先祖、宗族管理、设置族规、购置族产等方式来凝聚宗族力量,加强血缘认同,形成宗族文化。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宗族与官府也存在互动过程,官府支持宗族强化对族人的管理,借助宗族治理地方,社会秩序也得到维护。 [2] 如建立宗祠碑刻,安康市汉滨区将军乡金花村的《唐氏宗祠》,清道光十年(1830)刻立,记载了兴安唐氏始祖道忠,原籍为湖北麻城人,明朝成化年间迁至此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族人唐安明等合议立祠,其后唐氏宗祠屡有扩建;反映家族祖训家规的碑刻,如汉中市汉台区龙江镇谭堰村小学出土的《谭氏族规碑》记载了谭氏族规的16条款,明确了家族的规章制度和族人的责任与义务。
民间信仰是民众在历史中自发产生的对神灵、祖先、先贤的信仰和崇拜。乡土碑刻中的寺庙、道观、庙宇等创建碑的碑文内容是各地民众不同信仰的物化见证,能够反映古代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心理需求。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乡土文化,在凝聚乡村治理力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培育乡土情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 如对祖先的信仰,《清康熙二十二年氏族颂祖记事碑》记载康熙年间族人祭祀祖先之事;真武信仰,嵌于米脂县城郊乡宫庄村真武祖师庙前院左侧壁上的《真武祖师垂训》碑,记载了真武祖师教化世人多行善事,勿为恶,孝顺长辈,爱惜亲友,要守本分,遵法规,讲信用,否则将受天谴;观音信仰,《重修金堡观音殿碑